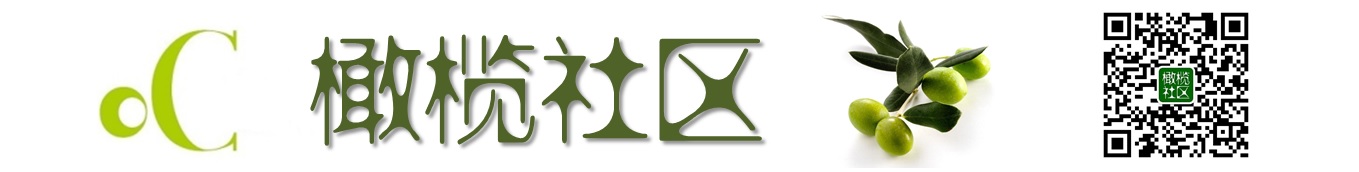信主以前,我的生活从外面看,实在不能算有什么波折。无论在国内考大学、出国读研究生,还是在美国找工作、定居,这一切都似乎通过最顺利的途径达到了。但是,当我走过这一段段人生旅程时,却自知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空虚。
不知为何,总觉得人生这样没什么意义。老是忍不住自问:难道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吗?总觉得在现在的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真正的”生活。在我生命的深处总有那么一股连我自己也不理解的力量,驱使我在已经有了的东西之外再去寻求些什么。好像找到了它,我才能得以完全。
当我为自己定下一个具体的目标,为之努力时,在外界的压力下,在追求的忙碌中,会暂时觉得好像只要达到目标,一切就会有意义。一旦达到目标,瞬间是很快乐;但是,平时那种生活没有意义的感觉很快就会回来。如果得到的是一项荣誉,那种胜利的狂欢也总是短暂的。
我也曾在爱情眩目的光晕中,觉得心上人似乎有奇异的能力,可以使我得以完全,结果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这种空缺也不能被知识所填补。在大学里,我学的是工程,对很多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很有兴趣。我发现看书和思考,往往可以让我进入一种精神高度集中、思维极为活跃的状态。我曾以为在知识和思想中存在着一条充满意义的人生道路。
这些年来,在学习和工作之余,几乎每一个关于人的知识领域我都涉猎了一点,也思考过其中各种发现所带来的含义。这些学习大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但也让我失望地看到:人类所有这些领域中已经获得的知识,都还不足以指导我走出生命无意义的状态。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无论思考的刺激和学习的乐趣有多大,它们还是填不满生活的空缺。
这生命的空缺也不能被艺术所带来的陶醉所填满。我非常着迷于欧洲的古典音乐。每一个音乐大师都带来一个独特的、彷佛超乎日常现实的奇妙境界。在那里,有日常生活中所不知道的满足。可惜的是,这些境界不能成为生命的真实。音符消散之后,我还是我,世界也依然如故,还往往显得更加苍白、平凡。
孩提时代,我所受的教育,所在的社会环境,使我感到似乎有一种叫理想的东西,可以使生命变得有意义。
虽然小小的头脑在理性上完全不懂理想的内容,“理想”所带来的那崇高、充实的感觉却是幼小的心灵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的。长大以后,对小时候所接触过的那种理想,在理性上早已不再认同。但奇怪地,偶尔听到那个时代的音乐,却往往在心灵深处勾起一种难言的向往。我也知道,无论人们对信仰有怎样情感上的需要,任何姑且信之的信仰代用品是无法真正、长期地满足这种需要的。
二十多岁的我,对生活已越来越感到疲倦。一件件可做的具体的事情,我都似乎去做了。但是,那模模糊糊中想要得到的幸福的人生,却依然和出发时一样的遥远,甚至变得更远。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战争的话,大多数具体的战役,我都似乎打胜了,但整场战争却在一天天地步向失败。渐渐地,我变得越来越懒散,生活显得越来越枯干。有时甚至觉得不如自杀算了,辛苦一场又有何益?
过去,我因好奇去过教堂。虽然有些教会的气氛曾让我有所感动,但总的来说,基督教于我是格格不入的。牧师的讲道总让我觉得既不合逻辑,又没有灵气。我也看不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抽象的信念,怎么能够解决我具体的苦恼。我所读过的一些哲学书籍,更让我觉得基督教在思想上是落后的,在历史上是阻碍进步的。
这时,一位好友信了基督。看到我苦闷的情形,便向我讲起基督教的信仰。我总是滔滔不绝地反驳回去。两年多后,当我自己也受浸信了主时,才知道原来从那时起,主便感动她在每天的祷告中为我的得救向主祈求。
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在她开始为我祷告后的几个月中,却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使我觉得,也许在基督教里真有什么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其中一件事是:那时,我买了一些巴赫(J. S. Bach)音乐的激光唱片,对他的音乐渐渐熟悉起来。开始只是觉得旋律优美动听。后来,慢慢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人生体验。它无法用语言来传达。我只能说:模模糊糊地,我觉得自己在音乐中接触到一个外在于我的巨大的生命源泉。
那泉水甘甜异常,当它漫过我心灵时,我感到有一种爱在抚慰着我的心。
这爱和人间的一切爱都不相同,是那么地无条件、那么地绝对可靠、那么地理解接受我的一切。
当这爱随着音乐源源不断地流过我里面时,我觉得有一种光明而圣洁的力量正将我提升到一种丰富而完美的存在中去。那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一种存在。这时,我会忍不住跪下来,流着泪轻声说:“神啊,多么伟大。”其实,当时我还没有相信神的存在,但这却是我的自然反应,犹如听到一首动听的舞曲会忍不住翩翩起舞一般。
虽然说不清,但我知道这种经验和我过去所有的音乐体验,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音乐向我所展示的境界,虽然不同于日常生活,却仍然不出我自己生命的范围。它们肯定我的生命,并使我的生命得以表达。但我在巴赫音乐中所遇到的,似乎是在我之外的另一个生命。一旦感受到它,那平时令我骄傲的自我突然显得那么局促、幽暗、贫乏。但这却不使我感到消沉压抑。因为那生命虽然和我的生命那么地不同,它却可以进到我里面来,和我融为一体,使我也带上它的宽广、光明和丰富。它不诱使我去背向周围的世界,而是让我充满一种新的力量去迎向这世界。它的效果也不随着音乐的终止而消散。每次经历过它,我就好像有什么地方被恒久地改变了。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受滋润和踏实的感觉。周围灰暗的事物也彷佛变得明亮起来。
伴随着这种体验的,是另一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当我在音乐中不由自主地跪下来赞美神的时候,往往在一瞬间,一个平时生活中难以解决的问题突然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呈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看到它,我马上就知道了问题的答案。
当我去听音乐时,完全没有去想这问题。这种光照来得那么突然,我马上的反应是:“这不是我的想法!”因为凡是我自己的想法,都带有一种我的“味道”;哪怕是把问题搁置一边几天后得到的“顿悟”,都不能免于这种味道。但这突如其来的光照,却几乎总是和我的思想方法相反的。在我看到它的同时,也马上看到了原来自己不知不觉之中一直运用着的思想方法是什么,它的局限在哪里。这答案真好像是在我生命所及的范围之外的。当我看到它时,我的生命彷佛也扩大了一点。
我的这些经历,开始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这和大家所认识的我太不相同了。渐渐地,我在心里越来越相信,自己所体验到的,是一种不能被人本主义思想体系所包容的经验。它似乎只能用“接触到神的生命”来描述。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想它,却十分愿意一再去经历它。最重要的是,不管我对这些经验怎么去看,这几个月来我生活持久不断地改善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到底是什么使巴赫写出这样的音乐呢?那些最让我动心的作品,其主题都与耶稣的出生、钉十架和复活有关。这使我开始怀疑在基督教里是否真有什么我所不知道的东西。
于是,心中萌生了再去教会看看的念头。但一想起我过去在教会的经验,马上又觉得这和我在巴赫音乐中所体验到的,高低相差实在太远了,甚而觉得去教堂简直是对神的不敬。
如此犹豫着,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我心中想再进一步了解基督教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我终于在那位朋友的怂恿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一次走进了教堂。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牧师所讲的,是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为了追随神的启示,他甚至愿意牺牲一百岁时才得到的爱子。当时,我马上想起弗洛依德的话:“基督教所宣扬的盲从使人的心理发展陷于孩童阶段。”
若是在以前,我一定会觉得牧师的话正好证明基督教的信息是落后的,甚至是有害的。但是,有了这几个月的经历,现在听起来,感觉却全然不同。我并不觉得亚伯拉罕是在盲从,反而觉得神在他的生命里一定是一样极好的东西,好过他的爱子。在亚伯拉罕过去的生活中,一定有什么经历使他对神的启示的信任超过他对自己理性的分析。
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究竟是什么呢?这吸引着我在第二个星期日再回到教堂。从此几乎不再中断,直到现在。
每次听讲道,都有很多东西令我不能接受。但讲道中却总有那么一些闪光的东西,让我愿意下次再回来听道。对教会里唱的赞美诗,开始时我也不喜欢,觉得旋律单调平板。慢慢地,却感觉到在这些简单的赞美诗里,也透露着和巴赫音乐中一样的从天上下来的生命气息。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不管是巴赫的音乐还是赞美诗,正是有了这生命才有了灵魂。在我以后的路上,赞美诗对我起了极大的帮助。又过了几个月,我才开始经常读圣经。与听道一样,每次读圣经的领受未必很多,但在去教会、读圣经一段时间之后,我却发现,自己从巴赫音乐中开始的那种体验,得到了大大的丰富、深化,和未去教会前的情形又大不相同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再看到神的生命的完美和我自己的局限。在祷告中、在每天的生活里、在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上,神把我二十多年来从未看到过的光照、从未体验过的感受放在我的心里。在我惊叹:“原来还有这么好的思路!”“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反应!”的同时,也一下子看到了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奉行着的人生的剧本是多么愚蠢而无效。
慢慢地,我意识到自己在思想方法、感觉方式、生活习惯上……都有那么多的缺陷和局限。它们像锁链一样把我层层捆绑住,使我活得又累又没有意思。它们是我内在的暴君,在它们的统治下,再自由的外在环境也不能带给我真正的自由。
我渐渐明白了为何圣经上说我们都有罪,这内在的暴君,正是罪。这些自然生命的局限,其根源在我们的遗传基因中即已存在。
它们从老祖宗亚当那里传下来,在母腹中胎儿里就已渐渐形成。我们还没有出生即已带上了罪。罪使我们的生命萎缩变形,导致外在行为上种种病态的表现。罪隐藏在我们所有思想的前提之中,使得我们的自我的反思不能揭示它,更不能帮助我们摆脱它。唯有神的启示,如同一道闪电,在照亮我眼前问题答案的同时,也照亮了隐藏在黑暗之中我生命的罪,又照亮了脱离这罪之牢笼通向自由的道路——神的生命。
圣经告诉我:这神的生命在耶稣基督身上第一次成功地和人的生命合为一体,因为耶稣是神子又是人子。因着耶稣,今天这神的生命也可以和我们的生命合为一体。这生命的力量,曾使耶稣冲破坟墓的限制,复活升到天上。今天,这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能让我们冲破由罪所带来的自然生命的种种局限,实现神给我们的潜力,进入自由之境。
以前我不承认自己有罪,却深受它的捆绑。现在意识到自己有罪,却并不消沉。因为主总是让我感受到一样更好的东西,回头才看到自己原有东西之不好。这是解脱,每解脱一个锁链,就体会到一种前所不知的新的自由。这是对自我的超越,无法靠着那个将要被超越的老我的力量去达到。
我觉得主犹如一位最好的老师,一步步地教我去把握住一种对世界、自我、人生全新的感受,教我慢慢学习去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充满喜乐和力量的生活。
奇妙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蓦然回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去问:“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了。
我生活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充实感里。我的心似乎不再被驱使着去寻求那使我得以完整的东西,对眼前的生活,渐渐多了许多热情和能量。
我不禁想起帕斯卡说过的话:“在人的心灵里有一块空缺,它的形状是上帝。”这空缺的存在使人感到深深的空虚,驱使着人们用各种方法去寻求能填补它的东西:财富、名声、爱情、理想、刺激……可是,无论高尚还是卑鄙,不管智慧还是愚拙,没有一样东西能恰到好处地将它填满。
唯有当神的生命流进人的心中时,我们才惊喜地发现:这空缺第一次被真正地、完全地、恒久地填满了。就这样,一种新的生命活力,带着光明、智慧和爱的感觉,从巴赫的音乐中开始,渐渐扩散到我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所流经之处,干枯的生命得到滋润。
不知不觉之中,内心那深深的空虚似乎在慢慢地被填满,生命没有意义的感觉似乎在悄悄地融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得到以后的喜悦,满足之后的安宁,其美好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以前曾在理想中看到过它的一点影子,现在却常活在它的里面。它非常伟大,却可以充满到最平凡的日常小事里,使之也变得有意义、有味道;它不是一套特定的人生哲学,而是引向各种真智慧的向导。它带来的不是一种对乌托邦的不着边际的幻想,而是实实在在的每日生命的更新。它经过我的心而流向我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却不起源于我心,也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它不同于我过去的一切经验,也不能被我所了解的科学知识来解释,它却给我带来人生至今最大、最实在的改变。
一年多以后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洛杉矶的古典音乐电台播放着巴赫的〈圣诞合唱曲〉(Christmas Oratorio)。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长达近三小时的音乐令我非常感动。乐曲的结尾尤其美丽动人。
在演出结束后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巴赫的圣诞合唱曲,在下面这些歌词中结束:耶稣已经打破了你身上的一切枷锁。死亡、魔鬼、罪和地狱都不再能捆绑你。人类已经在上帝的右手边获得了他的席位。”这一句句话似乎点明了我这一年多来奇妙的经历,它们再一次向我展示出那产生出巴赫美妙音乐的生命源泉。
此刻,神奇妙的爱感动着我,使我泪流满面地跪下来,按着圣经第一次对神说:〞神啊,我愿意成为一名基督徒。〞
本文选自《海外校园》第14期。作者来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