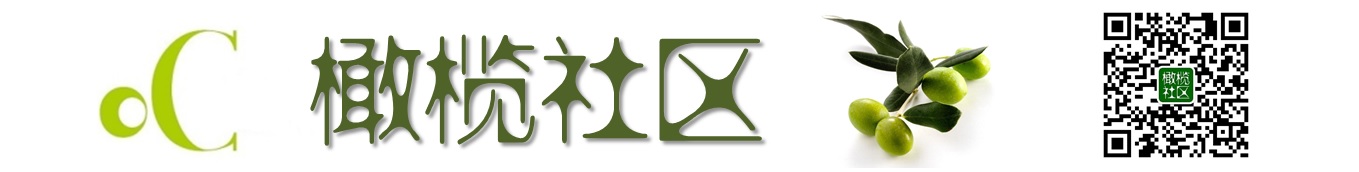本文原刊于《舉目》60期
莫非
 有位愛爾蘭聖經學者葛山(Dominic Crossan),形容後現代是黑夜中的大海,“在那裡沒有燈塔看守人,沒有燈塔,沒有岸。只有住在用自己想像所造成木筏上的人。”
有位愛爾蘭聖經學者葛山(Dominic Crossan),形容後現代是黑夜中的大海,“在那裡沒有燈塔看守人,沒有燈塔,沒有岸。只有住在用自己想像所造成木筏上的人。”
他的形容很圖像,把一個時代形容得如此黑暗,而且是在黑不見光的汪洋中,天茫地暗地漂浮,是一個沒有盼望,沒有方向,無人守候,海上無邊際的漂流。人活在其中,憑藉的,只是虛構出來的一個想像世界。
而在這個黑暗的汪洋世界裡,基督徒在何處呢?面對這個黑暗世界,我們的呼召又是什麼呢?
在這個破碎又斷裂的世界,對我們寫作的人來說,文字可以當作槳來划麼?是提供一個可以駛入安息的港灣麼?還是可以成為一座燈塔,來照亮黑暗中的大海?文字對這個世代,對這世代的我們個人,有什麼意義呢?
從信仰的角度來說,自然文字無法救贖靈魂,只有主耶穌可以。然而,我們卻可能都有被文字照亮,甚至燃燒的經驗。比如讀經,聖靈透過經上文字亮如火焰,熾熱我 們寒冷又迷惑的心。或者讀到一些好作品,文中的一、兩句話似黑森林中閃爍的星光,隱隱似乎望見自己從未說出的,也說不清楚的一些感受或關注。從文字中,我 們還可能看到自己的本相,像靠近燭火的鏡子,黑暗中浮出的臉,浮飄著深層的自己,陌生而又熟悉。
幸運地,我們更可能讀到一些生命的智慧或洞察,頓然讓人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悟。文字,此時好像變成了我們靈魂的殖民地,在其中對一些美麗的軌跡流連忘返。
被照亮是一種很溫暖、美好,也提升人心的經歷。因為在黑霧中,忽然有了“岸”的方向。
在這世界中,可能只有一種人不知自己是誰,也不知要往哪裡去,卻完全不在乎。那就是活得像巴斯卡所說的“死囚犯”的人:在面對死刑時,只願花時間扔擲骰子,卻不會想要推算自己究竟是怎樣陷入這樣的狀況?明日又將會發生什麼?
大部分人還是對自己的人生在乎,會想要找到“岸”的方向。文字和光的關係,就在於書寫信仰時,可以描寫光或光所照到的地方,賦予人一個方向。
書寫或創作本身,亦可幫我們從忙碌的生活裡,被吸引進一個孤獨沉思的空間。在那一人的天地裡,透過書寫,不論是對自我,生命和世界,都可以重新發現、認識和陳述。
文字又有一種特殊的能力,可以涉入我們深層的回憶和想法,提醒我們生存的複雜和神秘、醜惡和美麗。
某些方面來說,寫作也有點像信仰中的禱告,內含某種特殊力量,可以幫我們把破碎的生活經驗重新詮釋,轉變成一個更完整的世界。文字在整理之後,等於把一個更有生命洞察或更豐富的我們,送回到這個世界上來。
在文字中,我們也不只和自我對話,也在往外觸摸這世上另外一個靈魂,甚至,在文字中與上帝相遇。同時,讀者在我們的文字中,也可以指認出他生命中的一些事實和感受。
如此說來,作家是先從自身的經驗和苦難裡指認,因而生命得到整理和和認識,同時也有了語言可以分享。其他有類似經驗的讀者讀到後,便透過文字和作者們結合成為一種“社群”。這就是書寫。
不只如此,有位美國南方天主教作家波西(Walker Percy),還形容寫作是另一種方式的把脈。在文字中,揭發科學或醫學診斷不出來的病態。也許一個心理醫生會診斷為精神病的案例,文學裡卻可能呈現是屬 於人際關係裡的疏離,或是信仰的危機。而且,還會探討為何人與人會疏離?靈魂是從哪裡被自我放逐出來的?
基督徒作者的筆,就某些方面來說,也是另類哥白尼。
天文學家哥白尼曾提出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心論,說地球是繞著太陽轉(日心論),而非太陽繞著地球轉(地心論)。基督徒作者的筆,也可指出整個世界不是繞著我們轉(人心論),只有上帝才是這個宇宙的中心(神心論)。
而且面對人性,有時文學作者會比專家或學者更能回答一些問題:什麼是病態?什麼是險惡?什麼是人心的渴望?
很多拿起筆的人,都像聖經裡一些書卷的作者:大衛、耶利米、何西阿等,本身有自己的罪、傷口或軟弱。因此,他們獨具一幟的生命角度,在困境中可以清楚地指認出,什麼才是生命裡的真相。
自然,人生有許多方式可以走進真理,然後表述真理。但不可否認地,文字書寫是最有力,也走得最深的一種方式。
因此21世紀的人是在靈裡渴求中漂流,而這個時代需要點燈的人!
但燈塔看守人不是光,也不擁有光,他能作的,只是把光打到需要光的地方!對基督徒作者來說,也許不是每個作者都敢自許為燈塔看守人,但至少,我們可以用文字陪伴海裡漂流的人,一起游到有燈塔的地方。
因為我們都有軟弱和破碎之處,也有落海吃水的經驗,並深深瞭解什麼是漂流的滋味。更重要的是,因為信仰,我們說得出“腳踏實地”是怎麼一回事,知道恩典在生 活中出現的樣貌為何。因此,也可說用文字點亮或陪伴,而非律法式的教導或定罪,是這個世代每一位基督徒文字事奉者的呼召。
作者為《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主任,現住美國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