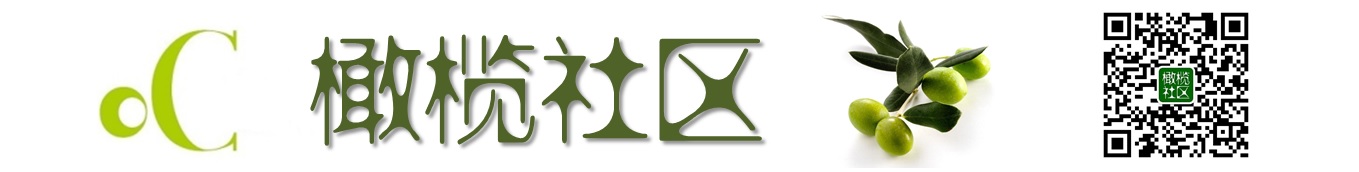李维森
从前,我是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这主要不是因为生活在无神论教育环境中,而是由于自己长期哲学思考的结果。
长期困惑的两个问题
我发现,假如把黑格尔逻辑哲学体系的最后绝对精神部份(即上帝)从他的体系中切除掉,其整个逻辑行程,即是哲学体系再现物质世界运动的过程。如果切除掉精神部份,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比苏联和中国大陆所通行的辩证唯物主义还“唯物”。当时,我曾想,像黑格尔这样思想深邃的大哲学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得出有神存在的结论的。
我思考很久,但没有得到一个较满意的答案。后来,当我读苏联哲学家古留加的《黑格尔小传》时,我似乎得到了一个解释。因为黑格尔当时所处的德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假如他不在其哲学体系中加上一个上帝部分,可能不保其在大学的教授职位。
大学毕业后,我更喜欢康德哲学,也再次涉及到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尽管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从本体论的角度否定了神在物质世界存在的可能性,从而为近代无神论哲学如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哲学开了先河;但在其伦理学的部份即《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又明确表示他相信神的存在与神的立法。与黑格尔不同,康德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哲学家。他的个人历史就是他的思想发展史。康德的人格决定了他是不会像黑格尔那样为了尘世的利益而向社会妥协的。
但像康德这样的人类思想巨人为什么也相信神的存在?我一直困惑不解。
另一个与神存在与否有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像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信神?如果说牛顿信神是因为他自幼生活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环境中还可解释得通,那么,生活在二十世纪的爱因斯坦信神就无法用此理由来解释了。对于这一现象,中国大陆哲学界有人专门进行过研究。
记得有一种说法是,当像爱因斯坦这样大的科学家研究宇宙现象规律到了极深的程度时,他们会发现宇宙是这样的奥秘无穷,而人的认识能力又是极其有限。这时,他们的心理常处于一种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为了保持内心心理的平衡,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其心理天秤的另一端加上一个砝码,即假定有一个上帝存在。不然的话,这些大科学家会疯掉的。这一解释显然是牵强附会的,
但当时我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解释。
尽管在出国之前,我是一个理性的无神论者,但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有机会读一遍圣经。我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了解西方文化,同时也是出于好奇。
当时,我认为,圣经对西欧和北美社会有着巨大影响。几千年来,圣经在许多方面塑造了西方人的伦理与价值规范。因此,要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制度的运作,不能不阅读一下圣经。可是,我发现,圣经中的一些经卷像神话,一些像历史,一些像小说。而新约的一些伦理教诲,读起来又觉得与儒家学说类同,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当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像圣经这样一本奇奇怪怪的书,会对西方社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所以读过一遍圣经,我并没留下多大印象,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与深思。
在出国之前,我虽然不信神,但我并不反对和阻拦我太太信基督教的上帝。当时,我和太太均在社科院工作。我太太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后,很快接受了其信仰。开始,我太太偷偷去家庭教会。后来,也时常去三自教堂崇拜。我也偶尔随太太去教堂。当我听教徒们高唱圣歌时,自己虽然不信,亦觉神圣庄严。看看周围基督徒虔诚的样子,常感到百思不解:他们在做什么呢?
一九八七年,我有机会公派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不久,我太太也带两个孩子以陪读的身份到堪培拉。八九年我再一次有机会读圣经。起因是在我交了硕士论文后,有一段空闲的时间。
当时,由中国大陆起始,后波及到海外华人文化界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方兴未艾。出于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向和未来中国道路的关心,我对这一东西文化大讨论的动向与文章一直比较留意。在八十年代中兴起的这场大讨论中,著名的哲学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1864-1920)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曾一度成为文化界人士讨论的热点话题。
韦伯认为,西欧和北美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心理原因,在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伦理。他指出,基督新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的救赎预定论、经济理性主义、以及理性化的主宰自己和世界的实践冲动和冒险精神,是引发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心理原因。
韦伯还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则是由于儒家文化作梗。他指出,与基督教新伦理中的理性地控制自己和世界的进取精神不同,儒家学说对宇宙和社会的看法有一种“强烈的今世乐观主义”,缺少“与世界的紧张性”。因此“在儒家的伦理中没有摆脱传统和习俗的内在力量”。
韦伯还指出,尽管儒家和基督教均主张理性主义,但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世界,而基督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统治和改变这个世界。这是基督教伦理能够、而儒家伦理则不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秩序之变革,以生发出资本主义之原因。
读到韦伯的这些宏论,引起了我再次读圣经的兴趣,而这次读圣经,是要从学术上“研究”它。但再读了一遍圣经后,我并没有从中找到所期望的韦伯的上述发现。当时,我也不理解韦伯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读第二遍圣经,对自己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无神论观念,亦没有产生任何动摇。
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我人生的道路进入了一个低谷。八九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后,转到另一家大学想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但由于没有拿到奖学金而不得不中途休学。为了一家四口生活之计,不得不到一家工厂打工。
这样,我暂时离开了十几年探索耕耘的学术“象牙塔”,进入了澳洲社会的底层世界。然而,这对我的精神的损伤并不大。因为,只是由于追求自己的学术目标而不得不做脑力劳动。加之,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的将来,我会回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去。
在这一时期,对我冲击比较大的是八、九十年代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急剧崩析。因为,自大学毕业后,我一直追求的一个学术目标是撰写一部成逻辑体系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经过多年的日夜思考,在我出国前后已形成了一个较清晰的理论框架。我实际上在努力探寻一个较民主的、人道的、具有市场机制且社会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我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制度的想法。然而,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巨变,使我突然意识到:问题不在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某种具体模式进行否定与改造,而是整个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就有问题。世界历史已证明这一点。
既然这一个制度本身已被彻底否定了,建立作为这一社会经济制度理论框架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什么意义?这样一来,十几年来我日夜苦思冥索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一下随苏东巨变粉碎了。追求的学术目标突然间烟消云散,自己的人生似乎突然变得没有任何意义,精神也几乎濒临崩溃的边沿。
在我人生道路进入低谷的时候,我太太已到一家华人基督教会崇拜。在我精神极端痛苦的时候,我太太和牧师劝我去教堂听听福音。当时,我的灵魂似乎在呼喊:神啊,你要是存在该有多好!只有你才能消除我心灵的无以名状的苦痛!
尽管当时我在内心里对神有一种渴求,但听到牧师所讲的福音,总觉得不顺耳。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牧师所讲的救恩道理总是不断地与自己几十年来所形成的知识框架发生撞击,又总是自己的无神论哲学信仰获胜。
一九九零年的圣诞节期间,我和太太带两个孩子一块参加了教会的一个退修会。在那里,我遇见了新加坡的黄聿源牧师。黄牧师发现我对神有所追求,就特别注意上了我。在三天的退修会期间,除了讲道时间外,黄牧师几乎全和我在一起。
在深入长谈中,我们的话题涉及到东西方文化、哲学伦理、宗教信仰和经济社会问题。虽然黄牧师从各种角度劝我信神,但我总有不相信有神存在的道理。我还坦率的告诉他,我不是不想信神,而是信不了。尽管自己情感上盼望有个神存在,但理性却告诉我,神并不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黄牧师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一个辨法,你回家后自己祷告吧!在你祷告时,你可以这样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向我显现。”
从退修会回到家中,我想起了黄牧师的嘱咐。当晚我试着第一次开口祷告。而祷告词只是复述黄牧师教我的话,只不过在后面加了一个“ 阿们”!祷告完之后,我就看经济学专业书。不一会,我感到疲倦,即和衣而卧。神即在梦中向我显现。我看见主耶稣站在一个高台上,大声地向我说了一句话:“你这个人太相信你自己了”!主耶稣的这句话,震动了我的整个神经。我随即醒来,发现是傍晚七点钟。
醒来之后,我对主耶稣的这句话沉思良久。是的,我是太相信自己了。回顾自已走过的生活道路,虽然自己并不常意识到,自信与自强是我个人生活、学术探讨和哲学思考的根基。我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村子里。后来曾在工厂作过统计与文书工作。七八年大陆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作过编辑、记者及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搞研究、发文章、做社会调查,以至出国留学,一步步似乎都是自我奋斗出来的。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上我一直非常自信。
虽然我曾喜欢过黑格尔,也崇拜过康德和马克思,但我相信自己认识和探索社会规律和进行抽象哲学思考的能力。是的,我是太相信自己了。
主耶稣的这一句话确实击中了我的要害。对于此事,我思考很久。这一切都是偶然的么?为什么我第一次试着祷告,主耶稣就向我显现,并说了这么一句话呢?于是,我似乎觉得有神存在。
自此,我亦开始热心去教会了。亦开始读一些与信仰有关的书籍,包括世界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信神的小册子、基督教神学、宗教哲学和科学哲学的书籍。并读了一些现代物理学最前沿的有关“统一场”和“大一统理论”的英文科普读物,以求证明神的存在。当时,有的牧师和基督徒问我:“你现在相信有神存在吗”?我回答说:“现在还不知道。等我证明了再说。如果证明不了,我说信,是欺骗自己”。
在这期间,我也第三次开始读圣经。可是,当我再读到圣经所讲的神六日造天地和耶稣三日复活的事,仍觉得与现代科学知识不符。在教堂里听到牧师所讲的救恩的道理,又与自己几十年来的思考与探索所形成的知识框架格格不入。听起来总觉得无多大意义,甚至觉得浪费时间。所以又渐渐不去教会了。
另一方面,由于我太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热心在中国留学生中传福音,而我却顽固的不信,我自然成了华人教会传福音的“重点”对象。不少牧师与在大学教书的华裔基督徒到我家与我促膝深谈,劝我悔改信神。
由于我圣经已读过,神学书籍也读过一些,他们要讲的我均知道,但我仍然不信,他们也无法说服我。在此期间,也曾蒙戴绍曾等海内外著名的牧师谆谆劝诲与代祷,虽有所感动,但理性上仍然顽固地抵抗神,以至当时不少牧师和教会的兄弟姊妹认为我是无可救药了。
可是,在此期间,我太太所参加的一个查经班的几位兄弟姐妹并没有 灰心。他们说:人是无法改变他了,只有神亲自做工,才能让他悔改。于是,他们决定每周的查经班后,专门为我得救祷告,求神亲自开启我心灵的眼睛。他们这样祷告长达年余,但我迟迟仍未悔改。
通过阅读大量与信仰有关的书籍,我虽然证明不了神的存在,亦证否不了神的存在。这时,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康德所说的“证明神的存在难,证明神的不存在更难”这句话的份量有多么重。
在差不多近两年时间里,我通过广泛阅读神学、宗教哲学和科普书籍的方法对神的探寻,完全误入歧途。结果,尽管自己主观上是想证明神的存在,但读的神学和宗教哲学书愈多,不但没能证明神的存在,反而更强化了自己的无神论信仰。
现在回想起来,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神是无限的存在,而人本身和人的知识均是有限的。想用人有限的知识去证明无限的神的存在,永远都是徒劳。本来,神的存在正像使徒保罗在圣经《罗马书》中所说的那样是叫人无可推诿的 。可是,神的存在又永远是不可能由物质世界的经验科学知识和形式逻辑证明出来的。任何想用感观世界的经验科学知识来证明神的存在的努力,只会导致无神论。
我在这一期间想用多读书和拓宽知识面的方法来达到认识神的努力,正好像用数加数的方法来证明数学中的无穷大概念一样。学过高等数学的人会知道,在数学中有一个符号∞,它不是一个数,但它大于任何数。不管你在1后加上一千个零或一万个零,它也不是无穷大。通过在1后面不断加零的方法来证明无穷大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你只是简单地假定有一个无穷大存在,整个微积分的辉煌数学体系就可以严密建立起来。
人类对神的追求亦是如此。本来,对任何一个心灵眼睛张开的基督徒来说,神的存在是简单明了,且时时、事事、处处可知的。没有任何神秘性。但是,假如有人用哲学和经验科学的知识来证明神的存在,他却永远达不到神。
回顾人类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从公元二、三世纪的诺斯底学派(Gnostics),到当代神学界巨擘田立克(Paul Tillich),从存在神学的鼻祖祈克果(Kierkegaard),到辩证神学的泰斗巴特(Karl Barth),任何人想用人的有限理性去证明或阐释神的存在,都只会引致无神论倾向的产生。因此,在自己刚对神的存在有所领悟时,阅读这些神学家的著作,不但没使自己更接近神,反而从某些程度上使自己信神更难了。
感谢神的浩恩大爱!祂并没有因为我的愚顽不化而弃之不顾。反而,神亲自做工,彰显巨大的神迹在我们家,使我直观地看见神的恩典而体知神的存在与神的大能。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女儿,一岁左右患了小儿麻痹症。开始,整个右腿不能运动。后来,经过针炙、推拿等传统中国疗法的治疗,右腿能运动了,但右腿肌肉萎缩,右脚畸形。
在出国前,我太太曾带着她跑遍几个省,寻医治疗。但是,由于两腿自然发育不同,两腿长短差距越来越大。到九一年,她已十三岁,两腿的长短差距达五公分,并且右脚跟不能着地。由于女儿每天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平时我亦习以为常。但一九九一年二、三月,有一天我在客厅看电视,发现女儿一瘸一拐地从我面前走过去。我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女儿正在快速长个子的时候。这样下去,大了将会是什么样子?
想到这里,我心如刀绞,泪水在眼眶打了几个转没掉下来。不几天,教会的牧师告诉我太太(这时我已基本上不去教会了),他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曾亲眼看见一位教授通过祷告治好许多人长短腿的问题。四月份这位教授要来墨尔本做一天的教牧事工讲课,问我是否同意为女儿祷告治病。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从心里根本是不相信的。因为,多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圣经四福音书中耶稣显神迹为人医病的事,更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但是出于爱女儿的心,我决定不妨一试。
到了四月二十九日那天,牧师带我们全家来到这位教授下榻的旅馆。进了房间后,华格纳教授搬了张椅子让我女儿坐下,然后平托起我女儿的双腿。这时,我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我女儿的两腿差五公分左右。接着,教授开始祷告。他一开始祷告,我就发现女儿的腿往外长。我即时激动的泪如泉涌。在短短一、二分钟时间里,我全家四口(包括我儿子)和牧师一起,亲眼看见我女儿的双腿长齐。
巨大的神迹,使我顿醒神的存在与大能:你不是几年来苦苦证明不了神的存在吗?现在神就亲自彰显祂的大能证明给你看!你不是不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吗?这神迹就发生在你眼前,就发生在这所谓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盛行的二十世纪!你到底信不信?
在上帝亲自的感召下,我再也无法不相信神的存在。一个月后我在教会受洗归了主耶稣。
受洗归主后,我曾在一些教会和华人基督教团契中为主做见证。一些人听了我的见证后,曾问我“你是不是由于看到发生在你女儿身上的神迹才相信神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沉思良久。然后,我回答说:“不”!回想自己十几年来所走过的生活历程,现在我可以清楚的醒悟到,从我开始读黑格尔和康德哲学思考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到基于了解西方文化的动机第一次读圣经,从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激发我第二次读圣经,到在澳求学受挫而进入人生道路低谷而第三次读圣经,这一切决非是偶然的。背后显然有神的步步引领。实际上到了一九九一年,经过长期思考探索,神已引领我到了一个信仰的临界点上。
这时,我虽然不能证明神的存在,却也再无法否定神的存在。神在我们家彰显祂的大能与爱,只不过进一步引领我跨过了这一临界点,进入祂的爱的国度。
当坐在教堂倾听赞美神的诗歌时,我享受着与神同在的喜乐与平安;当跪在书房向神祷告时,我沉浸在神的爱抚的甜蜜之中。每天打开圣经,总是发现一些经句,带着爱 、带着能力与权柄,像春风、像甘露,滋润自己的属灵生命。这是多么伟大奇妙的一本书啊!
在信神之前,我常常警钟自鸣:自己是搞社会科学的,而搞社会科学研究最需要的是思想的自由,最忌讳的是执拗的偏见和个人情感的喜好。因为执拗的思想偏见和个人情感的喜好往往会给一个人在观察社会现象时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因此,在信主之前,我曾一度担心,假如我有一天变成基督徒,基督信仰会不会限制我经济学思考的自由?这种担心在一个时期曾是我与教会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状态的潜隐心理原因。
但是,在信神归主后,我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对神的存在的信仰的确立,以及对圣经中真理的认识,不但不会限制你观察、分析和思考社会现象的自由,反而靠着神的启示,让你能够看清禄禄尘世中社会现象的本质。
亲爱的读者,当你有机会读到这篇见证时,你也许觉得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也许目前在你思想中有许许多多关于神存在与否的问号,也许在中国大陆所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些原理还阻碍着你相信有神存在。这都不要紧。
主耶稣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亲爱的读者,只要你心里愿意追求,只要你开口诚心祷告,神一定会亲自打开你心灵的眼睛,请你体知祂的存在。
本文选自《海外校园》第9期。作者来自山东省,曾任山东社会科学院《东岳论丛》编辑、记者和助理研究员。雪梨大学经济博士,于澳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