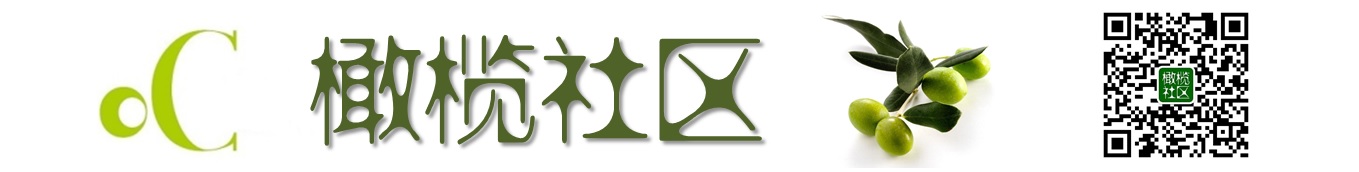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一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泰戈尔
我是一九九五年来到美国,和分别三、四年之久的妻子团聚的。老实说,如果不是妻子的坚持,如果不是担心婚姻破裂,我真不愿意来。
妻子仍在读学位,女儿也开始上小学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理当挑起分担家庭的经济重担。出国前,我在江苏的音乐学院里教了十几年的钢琴,于是我向洛杉矶的各音乐院校及各大学的音乐系申请工作。可是,以我那四百多分的“托福”成绩,别说当教师,就是当学生,音乐系都不肯收。
无可奈何之下,我去中餐馆当招待。但是不到半天,就因上错菜而被降成厨房杂役;接着我去加油站当收银员,又因不小心卖酒给青少年而被带上法庭……最后我在附近的一家衣厂找到了工作。
我,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坐在一群墨西哥小姑娘中间,从剪线做起 ,再学“单针”、“双针”……干足十个小时,赚到的钞票却还不及小姑娘的一半多……
这一切,都彷佛在告诉我,我在美国是一个废物。我的自信被击垮了 ,只剩下深深的挫折感。我捶着桌子问自己:为什么要抛弃已有的地位、尊严,到美国来出卖劳动力?我这样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在这里如何从头开始?又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愤懑和绝望,使我把所有的过错归咎到妻子头上,斥骂她只顾眷恋美国的生活。她则反唇相讥: “是你无能,怪不到我头上!”“无能”这两个字刺痛了我,更让我伤心的是,这恰好是一个写实。于是我大吼大叫,以掩饰自尊心的受伤,妻子亦大声回骂。什么伤感情的话都说了出来。
那一阵子,我的脾气坏得像脱缰的野马,完全无法控制;我的心,也像干旱的沙漠,没有一丝生气和快乐。
我的邻居,一个九十岁的老人,看到我家里这种情形,就叹着气对我说 :“你去礼拜堂吧。你这个样子,除了上帝,大概谁也救不了你了。 ”
我知道我救不了自己,而我又不愿我的生活继续这样下去,所以我真的去了附近的一个华人教会。
那天,牧师讲的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我当时觉得那是一个神话。不过,因为在教堂舒舒服服地坐着休息了一个上午,又受到了很多人热情的欢迎,我的心情很愉快,夫妻之间也和颜悦色地过了一天。后来,我得知教会的司琴临时因故离开,我便答应顶替一下。
我从教会借来歌本,试着弹奏。练习的第一首曲子是《先求祂的义》,“要求祂的国,先求祂的义……”曲调柔和宁静,有一种“朴素无报而众美从之”的气度。我的内心,有一处软软的地方被触动,而我确信那不仅仅是因为美丽的和弦。
礼拜日,我的伴奏很成功,大家都唱得很高兴。这是我到美国一年来,第一次受到夸赞。
就在这时,从江苏老家传来了噩耗,我的母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如果不是我这个独子离开,她也许能够及时获救的吧!我懊悔地以头撞墙,嚎哭不已,直到精疲力竭……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已恍恍惚惚地坐到了钢琴前,像段木头,只有双手在机械地弹奏。待我慢慢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弹一首歌《我的平安》。
我问自己,这是因为我太渴望它却得不到吗?这时妻子也随着琴声轻轻唱起“我将平安赐给你……这平安非世界所能够了解,藉祂知,靠祂活……”。
在歌声中,我听到一个慈爱的声音对我说:“来吧,到我面前来,卸下你的重担,接受我赐给你的平安。”
信主以后的日子,真是喜乐。生活仍然有不顺利,却不再有哭泣。每当我弹琴事奉上帝时,我都感到,旧的音符刚从指尖上流过,新的乐章又从心头迸出了。
上帝的恩典降临到我身上。教会的兄弟姊妹们纷纷把孩子送到我家跟我学琴,并且还介绍了更多的学生给我。我辞去衣厂的工作,专心教这些孩子们。我带着他们参加各种比赛,也拿了不少名次。
每当我用音乐事奉神时,内心就有一种狂喜。我用泰戈尔的诗谱了一首曲,那是我的心曲:“(神啊)当你命令我歌唱时,我的心因骄傲而迸裂;我仰望你的脸,泪水涌上我的眼眶。〞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美的谐音;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用我的歌曲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