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雪之陽
 我與老公在高中時即相戀。婚後4年,我們有了活潑可愛的兒子。我們的生活雖然平凡,但也平順。然而,自從老公被診斷出骨癌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們的人生已經不可能再“平凡”,人生之旅不再是一帆風順了。
我與老公在高中時即相戀。婚後4年,我們有了活潑可愛的兒子。我們的生活雖然平凡,但也平順。然而,自從老公被診斷出骨癌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們的人生已經不可能再“平凡”,人生之旅不再是一帆風順了。
就這樣,我們全家匆匆忙忙地踏上了這不平凡的旅程。
等於死,或等於生
我們彷彿陷入了絕境。正如莎士比亞所言:生,抑或死,這是一個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截肢手術,必須做!化療,必須進行!劑量,最大!時間,10個月!我們沒得選擇!對我們而言,不是哪個更好,而是怎樣才能活下來!
我問上帝: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是我們?你在創造的時候,不是給了我們自主意識和選擇權嗎?我們現在哪有選擇的餘地?
我質問,我憤怒,我恐懼!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它不容我擦乾眼淚,就排山倒海地湧來,將我們向前推,向前推。
一日,好朋友從遠方打來電話。聽完我的哭訴後,她說:在這樣的境況中,我們還是可以選擇:怨恨上帝,或信靠上帝。
聽完後,我一愣,細細想想,感受良多。選擇“怨恨上帝”很容易。對我而言,每天都是一場戰爭。苦毒、怨恨時常充滿我的心。我甚至在心中咒罵上帝。所以,選擇怨恨上帝、離棄上帝,是容易的。然而這樣的選擇帶給我的後果,是雙倍受苦。
第二個選擇,信靠上帝。這個很難。以前我很自豪,覺得自己對上帝雖然信心不足,但是有的。經歷這場災難以後,我才知道我是沒有信心。耶穌說:“你們要信服上帝。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他若心裡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可》11:22-24)
信心的功課很難,但艱難地選擇信靠主帶給我的,是平安、喜樂。
簡言之:怨恨上帝,等於死;信靠上帝,等於生。
拿起,還是放下?
有一首詩歌《除你以外》,這樣唱到:“除你以外,在天上我還能有誰?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別無眷戀!”
前一句歌詞,我心服口服。而後一句,我唱的時候,口是心非。在地上我還眷戀誰?我還眷戀我的老公、我的兒子、我的錢財。我心裡想,我信的這位上帝,還真是蠻容易嫉妒的。
的確,上帝宣稱:祂是獨一的真神。用別神代替祂的,愁苦必加增。祂愛我們,也要求我們盡心、盡力、盡意愛祂。我卻將祂的話置之腦後,因為我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我心靈深處根本不想做到。
這次經歷,讓我重新思考上帝的話語。我相信,上帝知道我們是做不到祂這個要求的,祂瞭解我們的本性是抓,而非放。那麼,祂為什麼還要求我們這樣做呢?
因為,祂愛我們!因為,祂知道,抓的後果是永遠的失去!
舉個例子:一天,老公呼吸困難,胸悶氣短,嘴唇發紫。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他患了癌症,都認為是心臟供血不足,於是給他服用了國內帶來的速效救心丸。然而,效果不佳。他又試著服下心絞痛的處方藥。服用後覺得好了一點。我們正開心的時候,他卻開始手腳發涼、呼吸困難。趕緊送急診,護士檢查和詢問後,對我們說:“如果他死了,死因就是你們給他吃的藥。”
事後我痛定思痛,領悟到:人是多麼有限!我們以為的“最好”,其實根本不好。我們拼命抓住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功名利祿,樣樣都要。然而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約》12:25)
所以,我們禱告:將我們的生命主權還給主,讓祂的旨意在我們身上暢行無阻!
自從老公生病以來,我努力扮演好所有的角色:妻子、母親、兒媳、女兒。
作為妻子,我儘量對老公溫柔、體貼。在醫院,我將地板擦亮,定時給老公榨果汁,不時給他按摩,時時給他讀聖經,同他一起唱詩歌……
連護士都說,我像陀螺轉個不停。我感嘆:陀螺只有在不停的旋轉之中才最穩定,一停下來,就會東倒西歪。
作為母親,我努力讓兒子生活保持正常。在醫院,我會打電話,告訴他,媽媽離你只有一通電話的距離。回到家中,我盡可能花時間和他在一起,滿足他的需要。小傢伙前一陣總吵吵去海邊,我知道我沒有辦法滿足他這個要求,但又不忍心直接拒絕。於是,我們去了附近的一個公園,那裡有一個湖,湖邊有很多的沙子。我告訴他,這是我們的秘密海灘。
作為兒媳,我在二老面前盡可能顯得輕鬆、樂觀,關心他們的飲食、起居。有時候,老人發脾氣,說一些氣話,我就打電話給好朋友發發牢騷,也就過去了。
作為女兒,我向父母隱瞞了此事。不是因為我堅強,而是不想他們擔心我們,而我們又要反過來擔心他們。因此,每到週末給父母打電話,我就迅速主動出擊,將家中每個人的情況問個遍。然後不等他們問話,就把電話給兒子。老人一聽孩子的聲音,就樂開了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這樣的日子中,我自我感覺越來越好,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新造的人,舊事已過,一切都是好的。
就在我飄飄然自我陶醉之際,我挨了當頭一棒——公公生病住院了。
那時老公第一個化療結束,身體剛剛開始恢復,也開始有了胃口,我們都很開心。那天晚上,我在心中盤算,要給自己放個小假,自我嘉獎一下。第二天早晨起床,一走出房門,就看到公公在吐。我耳朵頓時嗡嗡響,心裡很不是滋味。
送公公去醫院看急診。經過一番檢查、輸液和漫漫等待後,醫生讓我決定,是出院觀察,還是留院觀察。詢問過公公的意見之後,決定住院。
我的心情非常複雜。一方面,同情老人;另一方面,心疼自己。我怎麼這樣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樣的日子何時方休啊!我心中有苦毒。我甚至在心裡埋怨公公生病。
我不想禱告,覺得丈夫生病已經糟透了,現在公公又住院,事情還能比這更差嗎?既然已經壞到極端,就隨它去吧。我覺得正如《約伯記》22:2所言:“人豈能使上帝有益呢?”我們無論遭難,或是順利,都與上帝無益,甚至無關痛癢吧?
我對上帝很失望,我對自己更加失望。理性上,我明白公公很值得同情,我應該關心他、照顧他。聖經上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弗》6:2-3)但是,知道是知道,就是做不到。
住進醫院後,我勉強給公公用熱毛巾擦臉、擦手、洗腳。當晚教會的弟兄一到,我就如釋重負,立刻飛奔回家。臨走前,我說好第二天早上送兒子去托兒所之後,就來醫院。但是,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很沮喪,反復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是我?
把兒子送到托兒所之後,我坐進車裡,將音響打開,放聲大哭。我覺得委屈、不平和怨恨。最後,我調轉車頭回家,什麼也不做。直到醫院打來電話催,我才動身去醫院。整個過程就是《羅馬書》7:15-22的翻版——“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
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不能否認,這段時間,我很多地方做得不錯。然而正是這一點害了我,讓我自以為義。一葉障目,再也看不到別人的付出、別人的辛苦、別人的好。
我怎麼看,都覺得是我做的多,你們都不如我。我自己成了世界的全部,我與上帝隔絕,拒絕上帝進入我的世界。其實,我是逃避上帝的光,因為我不想看到自己的罪,我拒絕上帝光照我的黑暗。
這樣驕傲、狂妄和自以為義的後果是:我真是苦啊!心中充滿虛妄、苦毒和嫉妒,我滿懷委屈,憤憤不平,終日怨天尤人,好像全世界都虧欠了我。我甚至覺得自己在醫院表現很好,已經有資格對公公提要求了,我開始對他的信仰、價值觀品頭論足。
於是,一場信仰大戰在我家爆發。公公出院第二天,就召開全家會議,對我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警告我們不要再給他傳福音,他是不會信的。眾所周知,傳福音難,給家人傳福音更難。因為家人太瞭解我們的舊我,如果我們的信仰沒有改變舊我,反而讓我們平添了幾分優越感,那只會讓家人更加排斥和抵觸。
記得信主之前,有些基督徒向我傳福音,到我家中大講特講上帝的愛,還說,他們是因為愛我,所以勸我信。最後,他們總是會說:我會為你禱告的,希望你早日信主,早日蒙福。
我雖然口裡不說,心中卻頗不以為然:這些基督徒只愛上帝,不愛人。他們為了死後可以見上帝,什麼都願意做。說什麼為我禱告,他們關心過我的需要嗎?他們知道我生活中的困難嗎?
當我成了基督徒後,我又是如何做的呢?我想讓老人信主,也為他們禱告,可這真是因為愛他們嗎?
向家人傳福音最好的方式,是讓他們看到生命的改變。記得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參與了一個國家重點項目。因為是給國防部做的,很多試驗都要到偏遠的基地去。基地的條件都很差。記得有一次,我們凌晨4點起來,到一個廢棄的軍用機場做實驗。那裡有一個倉庫,蚊蠅滿天飛。我們就在那個倉庫吃早點。我沒有胃口,就把饅頭皮扒掉,只吃裡面的一點點心。坐在我旁邊的,是這個項目的總工程師,一位白髮蒼蒼的老教授。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默默地撿起扔在桌上的饅頭皮吃掉。事後,他也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提起。然而,我被深深震撼,從此不敢再浪費糧食。
我心中的隱罪,若非耶穌光照,我看不到;我口中的良言,若非聖靈感動,我說不出;我的生命,若非與上帝相交,不會改變。上帝啊,求你拿去我眼前的葉子,讓我看到你,你才是泰山,你才是至善至純的,讓我膚淺的生命與你相聯!
雖知“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前》5:16-18)但對我而言,喜樂很困難,灰心喪膽倒是常態。
老公的化療主治醫師,哈佛醫學院的教授,對我們說:“化療過程極其痛苦,會讓你身體的每一個部位都不舒服,甚至疼痛。作為癌症患者,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更會將這些疼痛放大數百、千倍,以致無法忍受。最好的辦法就是:根本不去想這些副作用。”
知易行難。化療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停地詢問化療的每一個副作用,以及相應的預防措施和治療方法。護士送來的每一種藥,我們都反覆確認名稱、用量、功效,及可能的副作用。有時護士晚來幾分鐘,我都會反覆催叫,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最終,我們醒悟了,“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17:22)。老公對我說:“我們把病交給醫生,把心交給上帝!我們要做的,就是安息。”
靈魂深處的安息是我們渴慕的,尤其是在波濤洶湧的日子裡。記得得知老公病情的那天晚上,我們倆徹夜無眠。手把手,眼淚不住流淌。我想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話。言語顯得如此蒼白無力。我們一宿不停地呼求主名,因為我們知道,此時此刻,人的勸慰是枉然的!
有人說我聰明,有人說我敏銳,有人說我特立獨行,但是從沒有一個人說過我堅強。我自詡柔弱是一種古典美,但是現在,我被推上人生大舞臺,扮演一個堅強、勇敢的角色。其實我的那點堅強、耐心、愛心和勇氣,早就用光了。所幸的是,我還可以向上帝要。
我需要耶穌,從早晨睜開眼,到晚上閉上眼,每時每刻都需要耶穌!信仰不再是經文和大道理,是糧食,是水。沒有它們,我活不下去。信仰不再是我生活的點綴,而是我每天站起來的力量源泉。
為了不痛,必須“劇烈的痛”
對剛剛截肢的老公而言,疼痛像熱戀中的情人一般,時刻不離。無論是坐起,還是躺下,無論是醒來,還是睡下,都苦痛不堪。
老公的疼痛有很多原因,一是來自刀口,是截肢手術造成的。這種痛開始比較劇烈,隨著時間推移,刀口漸漸癒合,疼痛也會減輕。另一類來自神經,因以前連著腳的神經切斷了。這種痛開始不太明顯,隨著時間推移,麻醉劑漸漸失效,神經醒來,疼痛日趨加重。
經過查閱資料和醫生講解,我們瞭解到,這種神經痛主要來自大腦,因為大腦不知道腳已經不在了,或者說,大腦拒絕承認這個事實。人體的構造真是十分奧妙、奇特,所有的細節都令人嘆為觀止。以血液循環為例,大腦發送命令,指揮心臟,輸送血液到人體的各個部位。那大腦如何知道血液已被輸送到腳呢?在我們的腳著地的瞬間,大腦便知道了,開始發命令,停止輸送血液,血液循環回來。但是由於截肢,老公的腳不在了,再不可能落地了,所以大腦就不斷命令輸送血液到“腳部”。大量血液不斷衝擊刀口,自然痛苦萬分。
我們問醫生,如何才能不痛呢?回答是:“劇烈的痛!”很意外吧?只有超乎尋常的劇痛,才能開啟大腦自我學習的潛能,認識到腳已經不在了,被迫接受現實。
世間萬事何嘗不是如此呢?我們若不受苦,怎會順服在上帝面前?若不受盡打擊,遍體鱗傷,又怎會尋求上帝的醫治?不順服會更苦,會遇到更多的打擊。只有接受醫治,才能得享安息!
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最近婆婆常常以淚洗面,我終於忍不住對她說:“我不是沒有眼淚,只是我捨不得在海濤面前流淚,因為他已經受了太多的苦!”
說完後,我心潮起伏。一方面,我認為自己是理性的,是在保護老公,也促使婆婆醒悟,她這樣的悲傷於事無補,不能達到她留下來幫助我們共度難關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的內心非常的不安,像有一團荊棘在我心中。有一個聲音不斷迴盪:你體諒過婆婆內心的傷痛嗎?你把自己藏在美、善、忍耐的面具裡,覺得自己還不錯,經歷了苦難之後,沒有很苦毒、很剛硬,還願意事奉,常常求上帝使用自己,但對身邊最需要、悲傷欲絕的母親,卻冷言相向,妄加評判!
我為自己的自以為是,感到羞愧。我不配基督徒的稱號!基督一直都在我的理性之中,在我的頭腦裡面,沒有安家在我的心中。我仍舊做我生命的主宰,我的生活、我的言行,仍被舊我支配。我用自己轄制基督,甚至褻瀆我的上帝。
上帝給的愛,我都照單收下。我明明知道上帝讓我經歷這一切的美意,是要我成就一顆基督的心,我卻成就了一顆自私的心,還加上了自以為義的剛硬、冷漠。什麼是基督的心?基督的心一定是一顆慈心!若沒有基督那樣的慈心,我們沒有辦法瞭解別人的苦楚;基督的心一定是一顆大心!若沒有這一份大心,我們沒有辦法包容別人的過失。
接納家人的本相不容易,接納長輩的傷害就更難。靠人有限的理性和聰明,根本沒有辦法做到的。但我們有萬能、超越的上帝,祂願意安家在我們心中,去掉我們的驕傲和戾氣,調和我們的性情、脾氣,我們是何等有福!
我對自己越失望,我才能越靠近上帝;我越是否定自己,我才能越靠近上帝。撕下美麗的面具很難過,但我寧願在真實中痛悔,也不要自欺欺人。
聖經說,真理可以使我們得自由(參《約》8:32-37,《林後》3:17)什麼是真正的自由?莊子在《山木》中寫下:“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是的,捨了自己的人還會痛嗎?還會對自己失望嗎?
然而,如何能虛己呢?靠修養、知識、聰明、學位,還是金錢?不,靠十字架!十字架又沉又苦,但背上十字架之後,卻必得真正的自由!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通訊專業,現居Boston。
圖片一由談妮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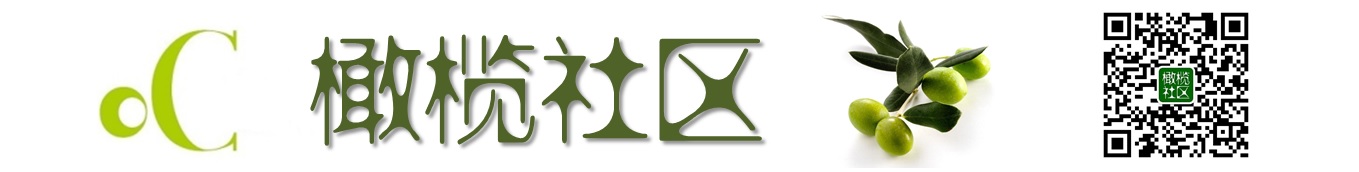


1 comment for “骨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