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62期
林約光
 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編註:華人教會習簡稱其名為“阿奎那”,但本文作者沿西方學術習慣,簡稱“多瑪斯”。)是中世紀最重要、體系最完備的神學大師。因為歷史因素,其神學洞見與貢獻,常被基督新教忽略,甚至遭刻意的曲解。由於中世紀(500-1500年)教會的腐敗,馬丁路德與加爾文也對整個中世紀神學與哲學持較負面的看法。然而,每一個歷史人物都是面對他那個時代的問題,因此,若不注意歷史的條件與脈絡,容易將不同的歷史條件齊一化。當代基督徒有責任以尊重、瞭解的態度,來評價歷史。
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編註:華人教會習簡稱其名為“阿奎那”,但本文作者沿西方學術習慣,簡稱“多瑪斯”。)是中世紀最重要、體系最完備的神學大師。因為歷史因素,其神學洞見與貢獻,常被基督新教忽略,甚至遭刻意的曲解。由於中世紀(500-1500年)教會的腐敗,馬丁路德與加爾文也對整個中世紀神學與哲學持較負面的看法。然而,每一個歷史人物都是面對他那個時代的問題,因此,若不注意歷史的條件與脈絡,容易將不同的歷史條件齊一化。當代基督徒有責任以尊重、瞭解的態度,來評價歷史。
有學者認為,亞米念主義與天主教的“與上帝合作”的救恩觀,是建基于多瑪斯的人觀,強調人的意志可以幫助人得救。多瑪斯真的認為,在上帝的恩典以外,人還可以依靠意志遵行律法,賺取得救的功德?那麼,多瑪斯是異端嗎?
雖然各宗派神學傳統都值得肯定。然而,每個傳統都有其限制,因此真理不應服膺於某一個傳統框架。究其實,這也反映出整個新教宗派意識的問題。
在本文,我要指出,多瑪斯是承傳奧古斯丁恩典與預定學說,在激烈變動的時代中,不困囿於時代的教會傳統,而是兼顧權威和理性,開創了新的神學體系與神學人類學(theological anthropology)的新典範。
早期宗教改革家對中世紀採取敵對態度,是可理解的。但我們距離宗教改革已有近5個世紀,我們理當更平和、客觀地對中世紀予以評價。具體地說,若形容奧古斯丁是為柏拉圖施洗並基督教化,那麼多瑪斯是將亞里斯多德予以基督教化;中世紀應成為我們信仰的遺產之一,而非羅馬天主教會的專屬。
以下我先將簡述多瑪斯的生平,然後從歷史分析他在神學人類學上的轉變,最後,要指出路德對多瑪斯的直接認識有限,以致不能給予正確的評價。
不可估量的貢獻
1225年,多瑪斯生於義大利羅課什卡(Roccasecca)阿奎那城堡的伯爵家庭,有3位長兄,5個姊妹。父親是倫巴第人的騎士,母親是那不勒斯的王公貴族。由于當時修道院在社會上的權勢地位,為前途考量,多瑪斯5歲即送到蒙第.卡西諾(Monte Cassino)的本篤會隱修院去學習。
多瑪斯的學術背景
1239年,14歲的多瑪斯進那不勒斯的拿波里(Neapel)大學就讀。這是為了抗衡受教皇控制的波隆納(Bologna)大學,由腓特烈二世皇帝於1224年設立的年輕大學。在這裡,多瑪斯除學習羅馬傳統7藝(Seven Liberal Arts)外,也開始接觸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工具論與自然哲學。
當時的拿波里大學不同於波隆納大學或法國的巴黎大學,不理會教會的規定,對於經阿拉伯人介紹翻譯而來的亞里斯多德作品,採取完全開放的作法。多瑪斯通過富吸引力的年輕學者彼得(Petrus von Hibernia)的教導,燃起對亞里斯多德的興趣,也造就他一生對哲學的喜愛。(註1)
此刻,以方濟各會和道明會為主的托缽修會運動,正在城市中如火如荼展開。多瑪斯傾心跟隨耶穌基督,嚮往理解信仰並傳揚信仰。1244年,19歲的多瑪斯選擇了較合適自己的道明會。多瑪斯的母親對此極力反對,甚至不惜軟禁他。過了一年,心志堅定的多瑪斯才折服家人,如願成為修士。
1245至1248年,多瑪斯在巴黎所屬修會念書,認識當時在神學哲學方面最出色,企圖將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自然哲學、形上學與倫理學全面引至教會的大亞爾伯(Albertus Magnus)。1248至1252年,多瑪斯跟隨大亞爾伯到德國的科隆,學習偽狄奧尼修(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gita)的思想,並完成4年的聖經神學學士學位(baccalaureus biblicus)——前2年學習舊約與新約的課程,後2年是彼得.隆巴多(Peter Lombard)的系統神學書《語錄》(Liber Sententiarum)。
1252至1256年,經大亞爾伯的舉薦,多瑪斯到巴黎大學,成為相當於現今的碩士生(baccalaureus sententiarius)並講授《語錄》(註2)。1256年,多瑪斯完成《隆巴多語錄四書論註》(Scriptum super quattuor libros sententiarum Petri Lombardiensis),相當於現今取得在大學授課資格的論文(Hablitationsschrift)。1256-1259年,多瑪斯正式成為巴黎大學的神學教授。
接下來將近20年,多瑪斯著作等身,有新舊約評注、哲學作品評注、問題集、神學系統作品,等等。他才智出眾,比同代人更敏銳地觀察到時代的問題。他是神學家,但他的哲學評註,比他那時代的人走得更遠,但對時代的挑戰也做出更多的妥協,以致他死後3年,還受到巴黎主教鄧比爾(Étinne Tempier)的譴責。
多瑪斯的思想脈絡(Geistesgeschichtliche Voraussetzungen),主要受兩個思潮的影響:經院哲學與亞里斯多德主義的交融,和不同於修道主義、重視福音使命的信仰。(註3)
經院哲學
經院哲學(Scholastik,也稱士林哲學)標誌著一種時代觀念,是一種科學(scientia)形式。這個形式有3種特徵:
(1)對傳統與權威的尊重態度。
(2)以審慎明辨的態度,權衡那些傳統及著述,藉由查考、論證、判斷的理性(ratio)來分辨。這符合“尋求理解的信仰”(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信仰準則。
(3)強調系統的、教學法的知識預備。知識不再是神祕的經驗、或是先知性的訊息,也不再是以“苦修-淨化”的方式,用來完善心靈,而是可客觀的獲取知識(Wissensaneignung)與傳授知識。這種授課與學習的操作方法,使知識成為每一個人都可領會、可檢驗的。(註4)
理性和信仰
理性和信仰,乍看之下,是對立的兩極。多瑪斯終其一生嘗試調和理性和信仰:理性以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形貌呈現,信仰則是有意識地回歸到福音最真實的信息。
基督教的第一個千年,受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很深,尤其通過奧古斯丁的介紹,此岸、彼岸的世界觀,靈肉二元論的人觀,宰控了整個基督教界。多虧12、13世紀亞里斯多德的承繼(Aristoteles-Rezeption),提供了另一種世界觀與人觀。(註5)
舉一例來說,多瑪斯的大學同事、方濟各會的波那文都拉(Bonaventura),因為承襲奧古斯丁傳統,認為人類獲得任何知識都需要藉助上帝的光照(illuminatio),輕看人生而求知的好奇心(curiositas)。
對此,多瑪斯不直接進行無謂的論辯,而是接受亞里斯多德《形而上學》的假設:人生而求知。多瑪斯認為,好奇心是自明的事實。並且,獲得自然的知識不需上帝特殊的光照,因為人類的理性即是自然之光,人可藉此獲得自然知識。但對於屬靈真理,人的自然理性有限,因此需要上帝的恩典與光照,方能領悟(註6)。多瑪斯在知識論、形而上學、哲學人類學與神學人類學等方面,帶給教會無可估量的貢獻。
基督教界普遍有一種錯誤看法:天主教著重功德,是因為多瑪斯的緣故。例如,奧爾森在《神學的故事》中說:“他(多瑪斯)教導靠行為得到救恩。”(註7)這是認為,多瑪斯相信半伯拉糾主義(Semipelagianism)。
什麼是半伯拉糾主義?按照《牛津基督教教會字典》,半伯拉糾主義指第5世紀的一群神學家,雖然不否認救恩出自恩典,但認為最初的信心出自人的自由意志,以後才需要恩典的介入(註8)。公元529年,奧蘭治第二次會議(Second Council of Orange),宣判這些神學家為異端,並肯定奧古斯丁反對伯拉糾主義的教義。
其次,半伯拉糾主義與信仰的發端(initium fidei)(註9)或預備恩典(praeparatio ad gratiam)的問題相關。要判別中世紀某位神學家是否是半伯拉糾主義者,可緊扣一個關鍵問題:人的自然能力如何(de potentia hominis ex suis naturalibus)?(註10)因此,人的自然能力的適用範圍(capacity),以及這些自然能力與救恩的關聯,是神學人類學的議題,即,人類學與救恩論的聯結點(Anknüpfungspunkt)。(註11)
多瑪斯神學人類學的轉折
無需掩飾,早期的多瑪斯在學習隆巴多的系統神學書《論注》(Scriptum)時期,態度確實模棱兩可,有半伯拉糾主義的色彩。他跟隨當時神學家的意見,認為人可以藉由自己的力量來預備恩典。(註12)
後來,他學習了奧古斯丁的著作後,特別是《論聖徒的預定》(De predestinatione sanctorum)與《論堅忍的賜予》(De dono perseuerantiae),多瑪斯拋棄早期立場,強調聖經的話,注重聖靈在信徒屬靈生活的內在工作。例如,他在《約翰福音》6:24的註釋中,說:“天父吸引許多人至祂的兒子,藉由那神性運作的直覺(instinct),由內推動人的心,使人相信:上帝自己就是那一位,在我們心裡工作,使我們既願意又能夠實行(《腓》2:13)。”(註13)
也就是說,多瑪斯成熟時期的觀點,與奧古斯丁完全一致——人的自然能力,在救恩上完全沒有任何價值,人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註14)。在多瑪斯的重要著作《神學大全》中肯定,人的救贖,在所有救恩階段(預定、初始稱義、保守人走向上帝、至福),都完全依賴上帝給每個人的自由與慈愛。(註15)
路德的錯誤解讀
路德也走過和多瑪斯相似的路徑。早期,路德在他的《語錄》旁註(marginal notes)中,毫無掩飾地顯現半伯拉糾主義的立場;轉變時期的《詩篇講座》(Dictata super Psalterium)內,也仍然殘留該立場的痕跡;及至《羅馬書註釋》,他才完全地擺脫。(註16)
過去,學界討論中世紀晚期的神學思潮,有晚期唯名論(nominalism)、奧古斯丁學派、晚期中世神秘主義,及多瑪斯主義(Thomism)。最近則有路德—多瑪斯的專門研究。其中一個課題,是探究路德到底有沒有讀過多瑪斯的作品?他是否明白多瑪斯在神學人類學上有過轉折?他對中世紀晚期多瑪斯主義的評價是否正確?
通過著名路德專家Janz教授的考究,我們得知,路德對多瑪斯的作品很不熟悉,他不瞭解真正的多瑪斯。因此,路德對多瑪斯的評論是不正確的(註17)。那麼,路德對晚期多瑪斯主義者的評論,又如何呢?
Janz教授認為,路德對晚期多瑪斯主義者不瞭解。路德甚至因為Karlstadt的誤導,將多瑪斯與“多瑪斯主義者的王子”Capreolus,看作伯拉糾主義者——其實,Capreolus正確地解讀了多瑪斯神學人類學中的奧古斯丁元素,並和路德最推崇的、中世紀唯一不被污染的奧古斯丁主義者Gregory of Rimini的看法一致。
因此,路德不僅對多瑪斯的解讀是錯誤的,對晚期的多瑪斯主義者的看法也不正確。如果較熟悉中世神學的路德都如此,那後來的加爾文也想必犯下同樣的錯誤。或許,在改教時期的學術方法與圖書資源,不允許他們進行像現代人一樣的客觀分析;而當時環境的動亂,也不容許有足夠的精力,去弄清事實真相。
結語
職是之故,現今的基督徒有責任回顧信仰的遺產。除非基督信仰只是純粹的信仰主義(fideism),否則,我們不能不理會與信仰有關的真假問題!願我們能從聖經、神學、歷史、哲學等不同的角度,用整體、客觀的態度看待歷史。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摒棄宗教革改家所遺留的不正確觀點,突破限制,回應時代,並見證我們的信仰。
註:
1. Maximilian Forschner, Thomas von Aquin (München : C.H. Beck, 2006), p. 14。對於多瑪斯的生平較新的資料可參考J.-P. Torrell, Magister Thomas. Leben und Werk des Thomas von Aquin (Freiburg, 1995)或J.-A. Weisheipl, Thomas von Aquin. Sein Leben und seine Theologie (Graz, Wien, Köln, 1980)。這兩本書皆有英文版本。
2. 關於中世紀大學的 授課與學習的制度,可參考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universities” in John Marenbon,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 (London : Routlegde & Kegan Paul, 1987), pp. 7-34.
3. M. Forschner, op. cit., p. 34-35.
4. Ibid., p. 33.
5. Ibid., p. 29-30.
6. F. Schupp, op. cit., p. 383-84.
7. 奧爾森,《神學的故事》,吳瑞誠、徐成德譯(台北:校園,2002),p. 410。
8.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rd ed.).
9. 關於奧古斯丁晚期對此觀念的思想,可參閱吳天岳,“奥古斯丁論信仰的發端(Initium Fidei)-行動的恩典與意願的自由決斷並存的哲學可能”,《雲南大學學報》9.6(2010/11): 10-27。
10. Denis R. Janz, Luther and Late Medieval Thomism: A Study in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 Press, 1983), p. 1。這個問題出現於隆巴多《語錄》卷二,辨別(Distinctions)25、 26、27、28、29、40、及41。可參考Peter Lombard, trans. by Giulio Silano, The Sentences, Book 2: On Creation (Toronto: PIMS, 2008) 。
11. Ibid., p. 6.
12. J.-P. Torrell, Saint Thomas Aquinas, Vol. 2: Spiritual Master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 of Amer. Pr., 2003), p. 209ff。Torrell教授引用多瑪斯的話: “In agreement with the other authors (aliis consentiendo), we say then that man can prepare himself to receive sanctifying grace through his free will alone.” In II Sent. d. 28, q. 1, a. 4.
13. In Ioannem VI, 44, lect. 5, n. 935. Torrell英譯如下:“But since external revelation and the object [in which one believes] are not merely the capacity to attract in this way, and since the internal instinct which pushes and moves us to believe has that capacity equally, the Father attracts many to the Son by the instinct of that divine operation which, from within, moves the heart of man so that he believes: ”參《腓》2:13;《何》11:4;《箴》21:1。
14. D. R. Janz, op.cit., p. 58. “It can now be said that Thomas’ mature teaching is in strict conformity with the Augustinian view that man ex suis naturalibus can perform no act which is of any soteriological value without the help of grace.”
15.參Joseph P. Wawrykow, God's Grace and Human Action: ‘Merit’ in the Theology of Thomas Aquina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16. D. R. Janz, op.cit., p. 154。關於路德的神學人類學的發展,可參閱該書第二章,p. 6-33;多瑪斯,p. 34-59;幾位多瑪斯主義者:John Capreolus, Henry of Gorkum, Conrad Koellin, 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 Cajetan, p. 60-153。
17. D. R. Janz, op.cit., p. 59.
作者為德國科隆大學多瑪斯研究中心博士生。
附注:
圖一為義大利畫家 Carlo Crivelli (1435–1495) 的作品。說明多瑪斯融合理性與信仰。此畫現存於倫敦的美術館
The National Gallery。
圖二為馮主恩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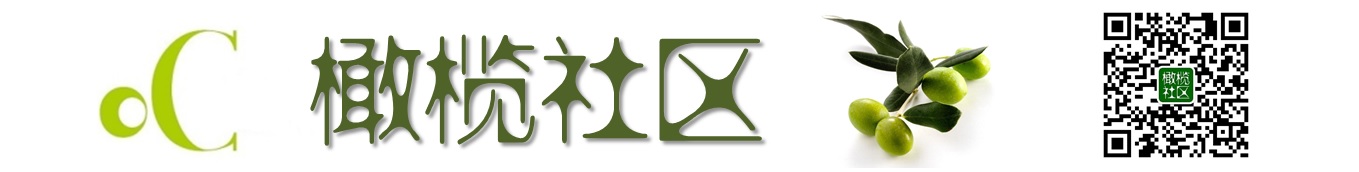

1 comment for “阿奎那,是異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