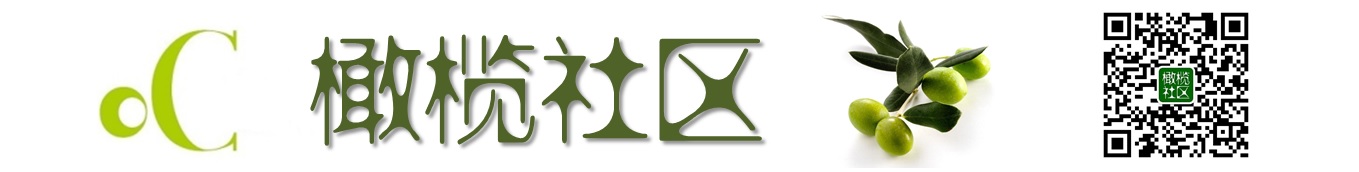我生长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我的感情丰富,天真活泼,性格外向。父母、老师都相信我能考入重点中学,将来能上北京大学,我自己也编织了许多美梦。
在小学毕业那年,“十年浩劫”爆发了,到处在造反、抄家、游街、批斗。升学考试取消了,学校停课了。
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对我说:“在1957年,我被定为右派份子……”渐渐地,彷佛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对我喊叫着“你是右派的女儿!右派的女儿!你是个黑五类!狗崽子!……”
那天夜里,我默默地哭了半夜。虽然只有十三岁,我已能看到自己的命运了。
我不再叫父亲。虽然,知道他很难过、歉疚,但我决心听党的话,与家庭画清界限,彻底决裂。许多夜晚,我睡不着,泪水湿透了枕头。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讲,这种在感情与理智、爱与恨之间挣扎和抉择是一件多么残酷痛苦的事啊。渐渐的,我变得非常自卑、胆怯和沉默。
一九六八年,北京开始组织毕业生上山下乡。像许多出身不好的人一样,我咬破手指写血书来表示决心,终于被批准去山西插队了。
离家那天,父母都请了半天假,妈妈说:“小红,我们不送你去车站了。小弟替我们去送你。”虽然有点失望,但我没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们的眼泪。告别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紧紧地盯住我,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深沉、痛苦、无奈的眼光。说过“再见”,他们飞快地转身离去,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尤其是爸爸那变得衰老瘦弱的身影,心中一阵冲动,「爸爸」的喊声已冲到嗓子眼儿,嘴都张开了,但还是把它强咽下去了。
我的目的地是汾河西岸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座落在一条山沟的顶端。住的都是窑洞,出门就爬坡。大部分耕地分布在几里外。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挑水。水要从山下的井里挑上来,一个壮小伙子需用四十分钟左右。那天,我们搀扶着,轮换着,歇歇走走,好不容易挣扎到了家。扔下担子,就都瘫在炕上。第二天早上,肩膀又红又肿,火烧火燎地疼,但还得去挑水担粪。担子一上肩,肩上像有千万根针在扎,头上直冒冷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是咬紧牙关还得干。
春夏秋冬,干那一样农活,不要脱几层皮呢?就说除禾,在三伏天,钻在一人多高的玉米之间除草,又闷又热。刀子样的玉米叶在脸上身上拉了数不清的口子,汗水流过,伤口钻心的疼。躺在炕上,骨头像散了架,浑身疼痛得睡不着。
我从没叫过苦或累。很快我干活就能和村民们一样了,可以担起百八十斤的担子和小伙子们赛跑。我们的肩上都长了厚厚的死肉。手掌上的血泡起了破,破了又起,直到结成了厚厚的老茧。我们都变得很像农民了,也都没再长个儿,一个同学还有点儿驼背,据说是被担子压的。
对我们来说,生活像是从天堂跌进了地狱。
大家相信的一直是: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世界上有亿万受苦受难的人民等待我们去解救。但实际上农民们的生活却是那样贫穷和绝望。我所见所经的与我以前所听所信的截然不同,使我的信仰开始从根本上动摇。
当时我不敢怀疑毛主席的话,对自己非常惶惑害怕,不停地在自己思想里找根源,对照毛主席的话检查批判自己,试图使立场重新坚定起来,但没用。
晚饭后,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场院的麦秸垛下,呆呆地望着满天星斗,不停地问着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但找不到答案。
我很快地变化着,天真、快乐再也不存在了,我变得非常悲观消沉。从“十年浩劫”后期开始,父母弟弟们先后出国,我的大弟凭自学考入清华大学,后来到香港,参加SAT,进入Princeton大学学习,这些被许多人渴慕的事和机会,对我都无吸引力。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里的“好了歌”,盼望早一天摆脱红尘。
也许正因这消沉、空虚和孤独,我草率地结了婚。但因种种原因,婚姻以破裂告终。这事也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一位朋友把我绝望的处境写信告诉了我在美国的父母。他们马上为我办理移民手续。
离开中国,那生我养我并埋葬着我的青春与理想的土地,我没有欢喜、悲伤或留恋。来到美国,踏上这千万人梦寐以求的土地,见到阔别多年的父母,我也不觉高兴。哀大莫过于心死。我只是一具躯壳。我已不会感觉,也没有感情,活着只是一种本能和为着一种责任。
美国宽松自由的气氛,又重享天伦之乐,使我的心灵开始复苏。我常常有一种深沉的哀痛,过去的经历会不自觉地浮现出来。我常边听《梁祝》边流泪。从音乐中,我重温我们那软弱、无奈、绝望的挣扎与破碎的梦。我为失去的一切,为我们那一代人,为在那片黄土地上继续挣扎求生的人们流泪。
我不敢使自己有一丝空闲,非常紧张地工作学习,以使心灵得到平衡。但这些都填补不了我内心的空虚。我常觉得人生太累了,也没有意义。所以当人和我谈到永生时,我就回答:“我不在乎永生,也不在乎下地狱。”
我已从一个天真单纯、娇生惯养的女孩子变成一个从社会底层翻滚挣扎出来的风尘女子。人间地狱的酸甜苦辣我都尝过了,我还怕再受什么罪或苦吗?我曾想,如果真有神,他能让我早早死去,永不再活,就是对我最大的慈悲与恩惠了。
到美国后,我最大的忧虑就是怕女儿交了坏朋友学坏了,所以我带女儿到纽泽西州若歌教会来,是为了让她交几个好朋友。这大约是1990年的事。
我参加礼拜,但我对牧师讲道不以为然。一些仪式让我联想到曾经经历过的偶像崇拜,使我不舒服。但那神圣、虔诚、和平、恬静的气氛常给我一种舒适的感受,好像使我沐浴在清晨温暖的阳光中,又好像柔和的春风在轻轻地抚摸我的心灵。教会中兄弟姐妹们的真诚与友爱也使我很感动,使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原来还有真诚。但我不习惯,我既渴望被人接受,又怕别人太接近我。
但是一谈到信仰,我就畏之如虎,实在是怕再受一次骗。多年生活在冷酷、虚伪与欺骗之中,我不再相信任何人、任何语言,只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再者,我一直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寄托,祈祷是一种心理疗法。经过了多年的风风雨雨,我自认为精神和性格已经很坚强独立了,不需要用一种信仰来支持我。后来我就不到教会来了。
一九九二年,我遇到一位从大陆来的基督徒。她对我讲述了她的经历。她们夫妇都是基督徒。解放后,她丈夫一面工作一面主持一个小教会。“十年浩劫”开始,她丈夫被迫害、批斗、游街,后来被抓走了,下落不明。直到浩劫结束,造反派的头头才交待出真情。她丈夫曾受到许多残酷的折磨,要他承认他信的神是假的。他坚决不承认,并坚定地声称自己是基督徒。最后造反派们说:“你既然坚信基督,那你就像基督那样死吧。”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十字架,把她丈夫钉上去,连那些交待的造反派们都说,她丈夫“死得很惨”。
在丈夫被抓走后,她和三个孩子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当时最大的孩子也只有十岁左右。她是一个医生,从未干过体力活,却要靠劳动来养活一家四口,生活的艰苦就可想而知了。她说每当要断粮时,主总是及时地供给她们。她的孩子们也常受歧视和欺侮。别的孩子们骂她们是“狗崽子”,打他们,甚至用纸包了粪便往他们身上扔。夜里,她不敢点灯,搂着三个孩子跪在地上,痛哭着向主祈祷。她说,全凭主的保守、支持和带领,她们孤儿寡母才能平安地度过那段困苦的岁月,三个孩子也都健康地长大成人。
当这位大姐流着泪讲述她的经历时,她没有怨恨和不平。看着她那像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的外貌,我想,应当有一位神,才能给她这种内在的坚强、平安与宽容。
她的见证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冲破了我内心自我封闭的屏障。我向她讲述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和内心的苦闷与彷徨。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在人前流泪,也是第一次对人讲心里话。我们边哭边谈直到深夜。她为我向主祈求,求主带领、医治和保守我。在她的鼓励和感动下,我表示愿意接受基督耶稣作我的救主。我觉得心里很轻松愉快。
但事过之后,我心里常常有一个声音在问,自己是否是在感情冲动之下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开始读经和祷告。我发现圣经读起来不再是那样枯燥无味,而是变得亲切了。我常作一些简单带有试探性的祷告。许多人都告诉我,不要试探神,要凭信心去信。但我对人、对己、对世事均无一点信心,让我凭信心去信,我实在做不到。
主并没因我的不信、试探和怀疑遗弃或惩罚我。神了解我的软弱和不足,并用祂的爱和宽恕来恩待我。
举个例子:当时我父亲和我女儿的关系很紧张。他看不惯我的女儿,认为她太美国化,又贪玩儿,不刻苦学习,所以常常会教训她几句。我女儿总觉得姥爷不喜欢她,不理解她,有时就会和姥爷顶嘴。这样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我被夹在中间很为难,天天提心吊胆,怕这爷孙俩又爆发一场战争。我尝试着为这事做了几次祷告,很奇妙,他们之间的冲突明显地减少了,关系也逐渐地好起来了。
当时还有许多事,主都回答了我的祷告。在主的启示下,我又回到若歌教会,并参加了Edison妇女团契。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从护士学校毕业,但因说英语的口音较重,一直找不到工作。我很灰心绝望。这时,团契里的伯母和姐妹们就鼓励我要
相信、依靠主,并为我代祷。很快我就有了一次interview的机会。当时我很紧张,也有些胆怯。在路上,我不停地祈祷,突然我心里有了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信心和平安。内心的感应告诉我,神已把这份工作赐给了我。
我的interview三天之后,就接到电话,为我安排好了第二次interview,在interview 时,护士长说:“如果你愿意,就留下吧。”这家医院还主动为我提供speach therapy帮助我矫正口音,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友善。
我于一九九四年八月受了洗。虽然我还是看不到摸不到神,但我常常感觉到神的同在。主常常垂听我的祷告,时时刻刻在看顾保守我。我也经历了神的爱和医治。
以前,我根本不能提过去的事,只要谈话一沾过去的生活,马上,我的嗓子里就像堵了一团棉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有人曾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你的心里压抑了太多的悲哀”,她说。神却奇妙地医治我心灵的创伤。我心里的哀痛和怨恨在逐渐消失,可以平静地回顾过去了。
就在我写这篇见证时,又读了几本有关“十年浩劫”的书,几乎写不下去了。是神使我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过去和那个时代。不错,我和中国的十亿人都在那个时代作了权利斗争的牺牲品,但我们的罪性和愚昧不也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吗?回顾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从奋斗、追求、挣扎、无奈、沉沦、堕落到绝望的过程中,许多人伤害过我,但我不也伤害过许多人吗?我们的罪性和私欲是这个时代堕落的根源,也是我所受伤害的根源。我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罪,就越感到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
当我向神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赐给我发自内心的平安和喜乐。神让我明白,只有从过去的罪和怨恨的捆绑中解脱出来,正确地看待过去,新的生命才能健康地成长,正像蝴蝶从蛹中蜕变出来一样。感谢神,祂卸去了我的重担,使过去成为我的鞭策和激励,使我能够勇敢地面对未来。
现在我不再感到生命像一条飘泊在愤怒的大海中的小船,也不再像一片无根的浮萍。主就是我的避风港,就是我的依靠。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消失,钱财、权势、名利、亲人或朋友都会离去或转眼成灰,只有主的爱是长存的。感谢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