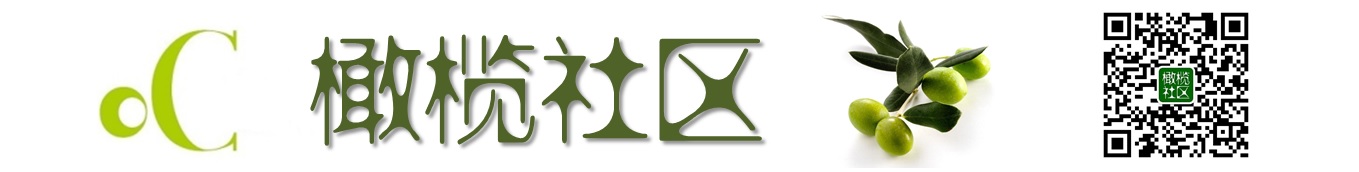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OC橄榄社区长期关注小组事工,请扫描图片上方的“OC橄榄社区”,选择“关注“,就可以收到我们定期推送的小组资料了)
虽然我认为牧师的讲道没意思,却感觉到教会的人很友好、热情,我很愿意和他们交往。当时教会有一位吕太太,很有爱心。我生小孩,她一次又一次地冒着寒风大雪,给我送鸡汤鸡酒。我小孩生病了,她帮我护理,买药送给我。尽管时间会流失一些记忆,但吕太太的那份爱心,却不时在我的记忆长河回荡。
我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但星期天很少去教堂做礼拜。有时被别人叫多了,觉得不好意思推辞,才应付去一次。就这样断断续续去了教会三年,后来干脆不去了。
1996年,当我们从加拿大举家搬迁到美国时,一位传道人岭先生和他的太太鼎力帮助我们。他们还为我们联系到了居于美国、愿意帮助我们的苏牧师,使我们刚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我们住的房屋,就是苏牧师帮着找的。苏牧师还带我去教会,带我查经,但我依然不肯信主,应付式地去了几次教会,也就不去了。
我不相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既然神是爱我们的,那他为何允许那么多的罪恶、灾难产生?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近代的“希特勒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革”、“六四”等等;从大到整个国家的倒行逆施、摧残人性、扼杀知识,小至包括我在内的个人的种种苦难,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被杀害,又有多少纯真无瑕的孩童丧失!神在哪里?他为何不阻止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
第二,我从未做过亏心事,为何要戴上“罪人”的帽子?我怎能和社会的恶人、无赖等同?听说人人都是“罪人”,难道对民族英雄岳飞和遗臭万年的秦桧,能一视同仁吗?
我来到充满希望、又富有机会的美国,岁月几乎又流逝了两年,而我依然只有满腔的无奈、失落。这个时候,我再次走进了教会。
去到教会,我有一种安宁感,彷佛有一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孩子!”我依稀感到一种美的盼望,这种盼望像在夜色中观赏树花似的,朦胧,令人冥想。
1999年,我去加州圣地牙哥参加了“China ’99”福音营。参加的有好几百人,都是中国的学人才子,都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当台上有人问:“谁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主?”大部分人都高高地举起手。然后齐唱“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边唱边流泪。泪水,涌自一颗颗圣光照亮的中国心,划过一张张真诚智慧的脸,溶集成一道生命的甘泉;歌声,带着圣灵的呼唤,美好的心愿,凝聚成一股力量,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这个激昂的场面,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的眼泪也无声地划下。透过这个场面,我彷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民族的盼望。透过这个场面,我理解了我当年嘲讽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救中国”的含义。
在参加福音营期间,我还在San Diego博物馆看到了一幅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画。画面非常逼真,那三颗钉子,就像真正的一样。任何人看到,都会有一种锥心惨痛之感。而这个时候的耶稣却说∶“赦免他们”对致他于死地的人们,他想到的是赦免,而不是恨、愤怒。上帝对人的爱,是何等的大、超过人类的想象啊。
这使我联想到,神所做的,远远超越了世人的思维。神为何不阻止人类的各种灾难,我不知道;但凭着我对他爱世人的信心,我相信他的主权。可见用圣经里的道德水准来衡量人,世人确实都是“罪人”。
我的另一个理性问题,“我不是罪人”,也解决了。我一直认为自己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聪明智慧;但对圣经的话语,很多都无法做到,也很难理解。
从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到我在圣地牙哥的“China ’99”福音营受洗礼,岁月流逝了七年。我在神的门前徘徊了七年,才肯真正进去。
对“罪人”的更深一步理解,则是在我决志信主后的第二个月。我的性格较倔,每次和我丈夫吵架,短则两三天不理采他,多则两星期不和他说话。我决志信主后的第二个月的一个星期六晚,我和丈夫又发生“战争了”,两人大吵大闹到夜里一点钟。然后他睡沙发,我则气得整夜难眠。
第二天,我憋着一肚子气,有点应付式地去教会参加崇拜。万万没想到,传道人正好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爱”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我一贯认为自己很懂得爱,且做得非常出色,但用这段经文对照自己,顿觉惭愧。
作者现居美国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