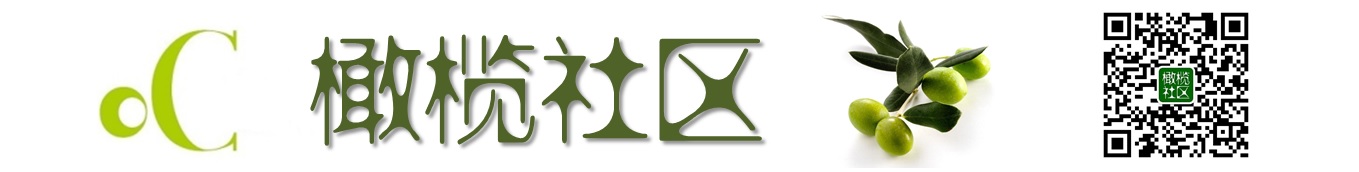朱明,一九九二年中国女子太极拳的银牌得主,她在美国的经历,是另一个“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
朱明,这位身材娇小的东方姑娘,在一九九五年巴尔的摩第三届全美武术比赛、一九九五年西雅图第一届国际武术锦标赛、一九九六年凤凰城全美武术大赛上,一人独得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四十二式综合太极拳、四十二式综合太极剑等十数块金牌。以致武术界有人传过话来,劝朱明下次最好不要参赛,言下之意,“奖牌大家拿拿”。
朱明不明白美国怎么也兴“共产风”、也发“红眼病”。她一甩小辫,微微笑道:“我只是才到山脚下而已,哪天真有一位大师指着我说句‘姑娘,你不错’,这比拿十几块金牌更令我高兴。”
朱明是“独行侠”,每次出门比拳赛剑她都独来独往,没有带队的教练,没有随行的队友,没有陪伴的亲人。真的,每次参赛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属于哪个国、哪个队,代表哪个门派、哪家武馆。倘若有人真要问她“行政隶属”关系,她一定含笑着回答,她属于“神国”。
每次参赛总有人问她要得几“金”几“银”,她会说:“No!有‘金’无‘银’,我向神求的只是金牌。”每次上场,她都要出声祷告,有人问她说些什么?她会说:“就一句,‘神哪,我是你的女儿,让我来荣耀你的名’!”
人人都说朱明 lucky,心想事成,金牌、绿卡、大学武术教师,要什么有什么。朱明会说:“真的,我就是世界上最lucky 的!”有人问朱明,“你为什么老说:‘神、神、神’,没有神你就不会成功吗?”朱明说:“这一位神是我亲身经历到的,我不能不说祂。没有祂的带领,或许也能得到金牌、绿卡、名誉、地位,但我一定活得很累。或许一辈子我只能说是‘活着’而已。”
有人要朱明作一个“残酷”的选择:“你要你的神,还是要你现有的一切。”朱明说:“神给了我现有的一切,若失去了这一切,我相信神还会让我重新得到。但若失去神,我想不出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朱明来美是准备好吃苦的。到洛杉矶的第二天她就做了保姆。第一锅饭里的水,她添了又减,减了又添;第一个菜酸甜苦辣,她想了又想,尝了又尝。两个月之后,她在《世界日报》上看到一家人刊出的广告,说是到这家做保姆,这家的律师主人可以帮着办身份。
朱明“跳槽”了,她真高兴,新的女主人是“祖国同胞”北京人,男主人是墨西哥裔的移民律师。整整四个月,朱明不但没有办成什么身份,连她原来合法的身份都故意拖“黑”了。朱明曾与女主人有过几段对话。
“请你帮助我到银行开个账户。”朱明拿着第一家做保姆时主人给了两张支票恳求道。
“你就把钱存在我的账户上,这样省力,什么时候想要,与我说一声就可以了。”女主人和颜悦色地说。
“我听说在美国,人人都应该有个社会安全卡,请你帮助我申请。”朱明恳求道。
“你不要听人乱说,社会安全卡那是开车的人才用的。你又不买车,你要那玩艺儿干嘛?”女主人说得合情入理。
“我的身份可申请延期,请帮助我。”朱明恳求道。
“我的丈夫就是移民律师,这还用得着找别人?他会给你办妥的”女主人每次都说同样的话。
朱明是凭着直觉预感到身后的陷阱。男女主人希望她变成一只畏光的蜗牛、乞食的笼雀,永远不敢走出他的家园一步。那天晚上,朱明表示等他们找到新人后她想离开,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她可以等。女主人见朱明主意已定,立刻变脸,扔给朱明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家不留外人过夜”。
朱明是自己走出大门的,再没有半句恳求的话,要是前面是大海,她也会跳下去的。她走得太急,急得连半年的血汗钱都忘了要。第二天朱明打电话要钱,男主人显得气愤异常:“你突然离去,二个孩子无人照顾,给我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我有权向你索赔。”
朱明再次打电话要钱,男主人恶狠狠地回答:“请不要再骚扰,你是非法居留,我有权告移民局把你递解出境。请告诉我你现在住在哪里?!”
身无分文的朱明拎着两个半年前入境时的包裹流落街头,她脸颊上的泪水是殷红的。
朱明被人领进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聚会。当她三言两语讲述完自己的遭遇,她怔住了,那些基督徒都围着她跪在地上,大声呼求神的怜悯、神的公义。朱明不理解这些堂堂七尺男儿怎么会有妇孺的心肠,她不明白这些强烈的肢体语言到底有什么功用。
不久,朱明得知妈妈因糖尿病并发症生命垂危,她失声痛哭。这一次她才算是明白了,这些弟兄姐妹会和她一起跪着流泪祷告意味着什么。妈妈出院了,朱明告诉妈妈,曾经有许多妈妈不认识的人,为妈妈呼求上帝。她告诉妈妈,这种无缘无故的爱不会来自人间,这些人好像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朱明有了自己的家,她不愿再离开,有段时间她不得不去远处做保姆,当她再度归来,见到久别的弟兄姐妹,用她自己的话说:“真想扑在他们的怀里哭一哭”。
朱明是极有悟性的,教她打拳的师傅从小就这么夸她。但极有悟性的朱明却一直悟不出人间世界评判是非对错的标准在哪里?她爷爷是个国民党军官,因“深明大义”,投诚起义,虽做了一个村夫,但政府一直另眼相看。算算爸爸称得上是个过黄河、渡长江忠心耿耿的革命军人,但最后竟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爷爷的“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以致被迫复员回老家。
学潮运动时她参加了游行,“先进工作者”资格被取消,还要接受组织审查。朱明一直在默念鲁迅的诗话,“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可那属她的“小楼”会在哪里呢?
93年初朱明来到了美国,她不懂,人人都说美国比中国好,然她所面对的却比原来更糟。还记得那家女主人瘫痪在床,那一位已经六十五岁的男主人却一点不懂自爱。保姆的房间是没有锁的,他每时每刻都会突然闯入。朱明每天和衣睡觉,用台灯挡门,在他面前练拳“示威”。一周后,朱明走了,她悄悄告诉下一位接任的小保姆,“小心啊,这里有狼!”朱明真的无法明白这个世界怎么漆黑一片,无论是中国是美国,人的心怎么都这样可怕、这样诡诈。
朱明一步步走向教堂,她想知道人们在那里干什么?音乐响起来了。噢,多久了,朱明忘记了自己还会唱歌,忘记了自己是个爱歌唱的姑娘。她试着张开喉咙慢慢合上了拍子,她身心灵深深地沉浸在虔诚、神圣、和平、清新的圣乐之中。
朱明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她要让身上每一个感觉器官,每一根神经末稍,每一只活着的细胞都来享受这美好的一切。她有点晕眩了,山涧的鸣泉跳跃着朝她奔来,她看到静卧在溪水旁休闲的小羊,她仰望苍穹,蔚蓝的天,白色的云,云罅透出的是橙色的阳光……音乐停止了。朱明真想一直听下去,一直唱下去,一直到她死去……
朱明快要受洗了。牧师问朱明,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是你不可饶恕的。朱明用发颤的声音讲完了她的故事。牧师说,神要祂的儿女饶恕人,就像祂饶恕了儿女一样。朱明点头时是咬着牙的。那天,朱明把心中难以承受的怨仇和苦毒全然地交托给了神。
朱明出名了,接连开设了三个太极拳班。有学生知道老师的冤屈,想要“替天行道”。朱明严严地制止他们,她相信神会处理得更好。
一年过去了。一天朱明与那位律师男主人在超级市场不期而遇,朱明问:“你还记得我的工资吗?”男主人的目光是躲闪的,他就像一个当场被捉的小偷。朱明说:“我信了神,神是公义的”。朱明笑自己俨然成了审判者。要是地上有缝,朱明相信他那一刻会钻进去的。男主人悻悻而去,朱明看到他苍老了许多,才一年他的头发就有些灰白了。
今天朱明有说有笑,像是在讲述一个不再属于她的故事。她对男女主人已经没有怨恨,她真的可怜他们,真的希望他们也能听到耶稣,能活得单纯一点,轻省一点,愉快一点,自由自在一点。
朱明走进了律师楼,她想知道被拖“黑”的身份是否能重新变为合法。律师说有可能,你可以走“特殊人才”的路,条件是你要有一个国际比赛得奖的证明。朱明越听越沉重,我连身份都没有,我如何自由出入境去拿奖牌呢?
一天,朱明的朋友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份空的西班牙国际武术比赛冠军证书。只要填上名就可以,就这么简单,连律师都点头。
朱明一度犯难。朱明想到了神,她脸红了,她跪在床前求神怜悯她的软弱,她对耶稣说:“我是你的女儿,我不能让你蒙羞。”
事隔三月,朱明在南加州武术比赛中小试牛刀,一气夺得三个第一,荣获“总冠军”的称号。多少次朱明跪在床前,感谢神使她躲避了诱惑,内心充满了浩然正气。那一夜,朱明依然跪着祷告,她看见天上的云开了,有大的亮光向她一闪一闪。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天后她在祷告中看到同样的景象。她将惊奇和喜悦告诉大家,大家都说:“这是异象,是神在领你走一条新路”。
朱明真是连做梦都没想到,没有多久,她就奇迹般地得到了第三届全美武术比赛和西雅图国际武术锦标赛的参赛机会,并得了六项冠军。这两场比赛是够水平的,前一场连美国总统克林顿都发了贺电。朱明顺利地取得了在美永久居留权,接着又幸运地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武术教师。
朱明曾经被轻视,曾经被欺侮,她曾经软弱、自卑,是神给了朱明生命的元气,将她从地上搀扶起来。朱明开设的第一个武术班是在教会中,她第一次踏上比赛征程,飞机票是弟兄姐妹送的;她走下飞机第一个前来迎接她的是当地教会的姐妹。
虽说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但朱明心中从未感到孤独,一本圣经、一盒圣乐一直伴随着她,即使在作暖身运动时她都带着耳机听着圣歌,她求神与她同在,求神让她紧张的心平静下来。朱明上场了,她说她感受到身后弟兄姐妹为她祷告的声势,一浪一浪涌过来。
朱明心存感恩,她免费在教会中开班教拳;她指头上有功夫,常无偿地为身边的姐妹按摩美容;她会修剪头发,排队预约的弟兄就再没有少过。
朱明不再悲咽、不再忧闷、不再自卑,她知道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为她开门。那一天,朱明喜极而泣,她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她有了绿卡,她可以回家团聚了。爸爸妈妈问她是好事为什么还要这样哭。爸爸妈妈越劝朱明哭得越凶。朱明说:“你们要为我感谢神,是祂救了你们的女儿”。“
是的,是的,”这位曾经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革命者”,告诉她心爱的女儿,他和妈妈已经在读圣经,已经会作祷告。“别哭,别哭,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
朱明破涕为笑,“共同语言”,爸爸说得多逗。等她回家,她要问爸爸,在劝她“别哭”的时候,他自己有没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