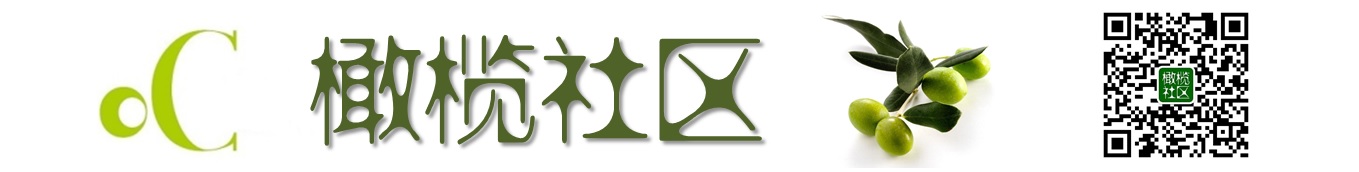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OC橄榄社区长期关注小组事工,请点击图片上方的“OC橄榄社区”,选择“关注“,就可以收到我们定期推送的小组资料了)
只看后脑勺
同样,科学也在受审判之列。当科学家告诉哲学家“世界是这样的”,哲学家总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必然是这样的么?”哲学不会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一旦发现,就希望推倒重来。所以,搞哲学就需要极大的勇气,至少需要比自杀更大的勇气。
科学家看问题是“正思”,哲学家看问题是“反思”。哲学家看问题就和职业刽子手看人一样。刽子手看人不看人的容貌美丑、气质高低,他们只看人的后脑勺──哪里好下刀。当一个理论或教义摆在哲学家面前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相信。他会先审查一番,看看哪里好下刀--怀疑、挑战、驳倒。打垮人家的王国,建立自己的,然后披袍登基。最典型的例子是康德,简单地说,他把上帝在理性的王国里“杀死”,又在道德领域里让上帝复活。
基督徒讲“耶稣之死”对人类有极大的道德启示力量,因为他为赦免人的罪从容赴死。我说,这算得了什么,苏格拉底之死不靠任何外力的帮助岂不是更伟大?更何况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叫∶“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是否显示在最后时刻,连他都动摇了对上帝的信心了?至少这也是一个疑点嘛。既然耶稣赴死复活以赎人的罪,两千年快过去了,人口翻几十倍,人类犯下的罪也更大,为什么他不会再来一遍?
关公战秦琼
例如,逻辑学里常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那么,上帝能否创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对这一个逻辑难题,无论你回答是或否,你都会掉进一个陷阱里,且出不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和引起数学史上第三次危机的“理发师悖论”(又称罗素悖论,是罗素提出的),在逻辑形式和语义结构上是等价的。
一日他自己惶惑起来,要不要给自己理发?如果理,那么我是“自己给自己理发的那种人”,按照广告的原理,我就不应该理。反过来,如果我不给自己理,那么我是“那种自己不给自己理发的人”,所以,我应该给自己理发。把它换成数学的形式,就是“对于一切不属于自身元素的集合A,当且仅当A属于A时,A不属于A;反之亦然。”
如此简明的悖论,引发了数学、逻辑学乃至整个理论科学界的大地震。当1903年罗素把这个悖论告知当代分析哲学的开山之人--德国数学家、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弗雷格,弗雷格说∶“这将引起整个演绎理论的崩溃,我真的希望你没有发现它。”(注1)
后来,虽然发展了“类型论”、“模型论”来限制定义方式,以消除矛盾,但始终不能令人满意。(上帝与石头的悖论和罗素悖论的逻辑形式问题,绝非此处一言两语所能解释清楚,它的反向形式与罗素悖论不同。从语义学的观点看,被定义和说明的概念又在定义项中使用了,是典型的悖论语言结构。上帝与石头悖论的解决方式是一个很复杂的限定模式。总之,它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不是神学问题。)
直到再后来,大数学家哥德尔发现了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将数学基础研究的哲学意义,揭示得更加明显。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是说∶当一个演绎系统是自足的(不矛盾的),总有至少一个或几个前提是在系统内不能证明的。例如,在相对论中,光速C恒定且最大这个前提,就是不能在相对论演绎系统中证明的。
我并不想把数学的危机问题引入宗教问题的争论中来,尽管一个美国数学史家,在谈到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时,干脆称“数学,神学的一个分支。”(注2)但第三次数学危机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在哲学的意义上是明显的∶它宣告并且证明人的理性、理智不是无限的,人类必须在大自然的秘密面前保持谦逊的态度。回到“上帝与石头的悖论”,我们会发现,我们自以为扔向上帝的坚硬石头原来是一个鸡蛋,不仅没能把上帝打死,自身反而撞了个粉碎,让我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不如鼠挖洞
但我明白教会与教义本身的区别,所以,带着两个问题重读圣经及有关的书籍,心想,第一,如果圣经为十字军、裁判所的暴力提供充分的根据,我就坚决不信,宁下地狱也不信。第二,如没有根据,但我所去的教会,不能诚实面对此历史事实,那么我也不再去。
第一个问题,虽然我没有从圣经中找到直接的根据,但有一段时间,把《旧约》上帝的惩罚当作间接的证据。特别是逾越节(编注∶见《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来历让我感到恐怖。尽管《新约》中有很多上帝“爱的教育”,也不能抵销这种恐怖。我有时感到圣经肯定有问题,新旧约中的上帝简直判若两人。这真让我再次陷入困惑和怀疑。
虽然星期五的查经还去,星期天的礼拜是不去了,我不愿意对那样一个形像的上帝表示任何敬意,尤其不愿意念诵主祷文。当我念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这正令我想到政教合一的中世纪!
至于星期五的查经,也打算随时停止。但我还想多了解一些,就提醒自己∶这也许是自己误解呢。至少,可以当作积累批判素材吧。总之,这个时候我的想法就如齐克果所说的∶“要么相信他,要么冒犯他。”我常常一边听讲查经,一边提出一些问题发难。
有一回,我提出,从《旧约》看上帝,上帝根本不像有大爱的神,倒像一个野蛮部落的酋长。我心里想,我说了这种亵渎神明的话,估计教会的人可能这一次敷衍过去,以后就会不理我了。没想到,有一位弟兄一边叫我多全面地看圣经,一边说帮我祷告。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他在为我着急,但对我仍有大的信心。这样,我就又多看了一些书--圣经和关于圣经的。
当然,我不会全看护教的、教义的书,因为我已经养成了正反看问题的习惯。我重读了罗素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和尼采的攻击基督教的书籍。这个时期我实在是痛苦,心灵再一次成为交战的战场。心中一个声音说,上帝如果存在的话,早该给联邦调查局的人抓去,并以战争、杀婴、滥用生物武器等多项罪名起诉;另一个声音则说,人应该有明确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最好的信仰。
每当我星期五去教会时,我就对天祷告,若真有上帝,就请你开导我。也许是日有所想夜有所梦吧,有几次在我打盹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声音说∶祷告有什么出息,你应该起来坚决批它,比过去更有力地羞辱它。退一步说 即使真有上帝,像你这样一个过去亵渎神明的人,也不会被接纳。
这种梦发生过两次。教会的那位弟兄说那是“魔鬼的搅扰”。我说像我这样的小人物犯不上啊!
我是不相信魔鬼的,我宁愿相信这是潜意识对我内心矛盾状态的真实写照。我也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赶鬼。因为我有我的想法,第一,我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没有什么能完全驾驭我。第二,对付一切妄念、狂热、乱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找一个尽可能中立的立足点重新反省自己。第三,真有怪力乱鬼,对付的最好的办法是置之不理,见怪不怪,使其自败。第四,我实在不想拜神不成反召来鬼。
这些理由,在基督徒看来,是没有信心的标志。可是,这个时候没有灰心就不错了,哪里还谈什么信心。说来也怪,我的心真的在一个新的立足点平静了、站稳了。这个立足点就是,摆脱当今的暂时的、变化的价值观看问题。譬如,对古代吴起杀妻求将,我们能理解,何也?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变换了道德观去理解那特定的时期。
于是我重新思考关于死的问题。首先,死亡在神眼里与在我们眼里肯定是不同的。人以死为毁灭,神以人之死为新的开始,或送入天堂,或打下地狱。第二,就是在人的眼里,不同的民族,或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期,对死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拿中国人来说,在战国以前和汉代以后以及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证明,秦代以前,中国人没有像现在这么怕死。“鬼”按照说文解字上说,鬼者,归也。死实际是一种回家。
远方的客人
当我读到,巴特说“圣经不是一本人关于上帝的书,而是上帝关于人的书”,及“因为从人的角度看,《旧约》里的战争杀戮一切都太轻易,似乎太草率。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太多”。
到此处,我的“老鼠洞里”,突然进来一丝亮光。再重读圣经,“可是朋友啊,你是谁,竟敢跟上帝顶嘴呢?一个瓦器怎么能对造他的人说∶‘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子呢?’”(现代中文译本《罗》9:19)“人不可自欺。要是你们中间有人按照世人的标准自以为有智慧,他倒应该承认自己的愚拙,好成为真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所认为有智慧的,在上帝眼中却是愚拙的。正如圣经所说∶‘上帝使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另一处经文说∶‘主知道智慧者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妄想。’(现代中文译本《林前》3:18~20)”
我感到这话简直就是对我说的,真是“一语真醇万古新”,更何况圣经里这种话比比皆是!
按照圣经的记载,神人失和的关键就在智慧果(善恶果)。所以世上自以为智慧的就是我这种的,理应多吃点苦头才对。
经过几天暗暗发问“信不信?”以后,我终于点头∶信。凭什么?凭一无所有和一无所知。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无知。必须打扫自己的心灵,就像打扫房屋迎接远方的客人。“你所盼望等待的尊贵客人就要到来,快把你的门窗打开。”(泰戈尔)
智慧止步处
固然,奇迹能使人在震撼或恐怖中产生信仰。但是,这样产生的信仰不会长久,也就是说仅靠奇迹产生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看看耶稣在什么条件下才行奇迹。巨大的信心、盼望、热爱!(《可》1:40,2:1-12,《约》11:33-40)。没有这三种或之一,怎么配见奇迹?
耶稣在拒绝法利赛人的时候,透露出这样的讯息∶假冒伪善的人啊,你们信了才是最大的奇迹!
另一种“去了奇迹我就信”,这常常是自以为是的理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那意思分明是说,耶稣所行的不合人类的理性,所以我不信。我过去也持这种观点。现在我明白了,假如真的把耶稣所行的奇迹全部拿掉,只剩下常识理性的东西,那么,我们还真的会信他么?
绝对的尺度
“罪”是圣经的根本观念。中国人很难接受,为什么?我们固有之文化浸在儒道佛等人的智慧所发明的宗教中成长,总免不了“洋洋自得”。想一想,基督教曾三进三出中华文明,最长的凡200年,竟然如水涤荷叶,不留痕迹,个中原委与中华文化(汉代以后)关系重大。
原罪是一把绝对的尺度。在此尺度下,没有人能够洋洋自得,更扫除了任何人的自我崇拜、他人崇拜。这个标准之下,人类的任何自相残杀都失去了根据。这把戒尺,把任何以正义伪装起来的把戏都戳穿。这把戒尺,在一个极限上洞视着人的腐败。
看看我们文明里最发达的是什么?不是数学逻辑,不是科学知识,不是民主文化,而是攻克杀伐的理论--兵法。从姜太公,孙武,到毛泽东,出了多少兵书?在这一点上倒是雄居世界之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杀人斗人没有禁忌,技术又实用,所以,人斗人什么办法都可以想,人所能想到的酷刑中国都有。是故,鲁迅先生说∶“中国历来不乏杀人之术,酷刑更是世界第一,连发明宗教裁判所的人都会自叹不如。”我爱我们的民族,但我不得不哀叹,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民族。(值得别的民族庆幸的是,虽然窝里斗可能随时随地发生,但汉族很少主动进攻别的民族。)
很多人都想当“无罪之人”。义人,盼望耶稣能给几个名额,这样可以争取。耶稣看透了人的诡计,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都没有!”(《罗》3:10)。完了,这一下彻底完了。一个名额也没有,那就连假冒的可能都没有了,做假文凭的都失业了。
我尝到甜头,开始领略教义之美。
从感性上讲,基督教教义是不美的,因为它启示的真理直指人性的真实状态。它正像《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照出了人的真实状态--一个骷髅,但它可以治病;相反,另一些宗教如风月宝鉴的另一面--一个美人在向你招手,但她会要你送命。
换一个角度说,基督教启示给人的道德真理,从理性的角度看,不管你信不信,是美的。
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有限的理性不可能认识无限的秘密,因此信仰是必须的。
枷锁与自由
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不是的。卢梭说的是用世上的标准来衡量的,是虚幻的。一个婴儿的自由意谓着什么?谁敢给幼儿绝对的自由呢?但我们没有人误解卢梭传达的讯息∶人类渴望自由。
人刚出生,智力体力都是柔弱的,是处在枷锁中。随着成长,会在原罪之上加更多的罪,罪蒙蔽了人的眼睛。瞎眼之人又有何自由可言?人唯有因信称义,才能得自由。“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教训,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你们会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得到自由。”(《约》8:31-38)。说到底,人生最大的枷锁就是人的理性贫乏和远离真理。
基督教义就是“天理”,耶稣的话就是渡船。有的道看似荒诞,原来是正言若反;有的话看似无法无天,原来铁证在你,大言不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