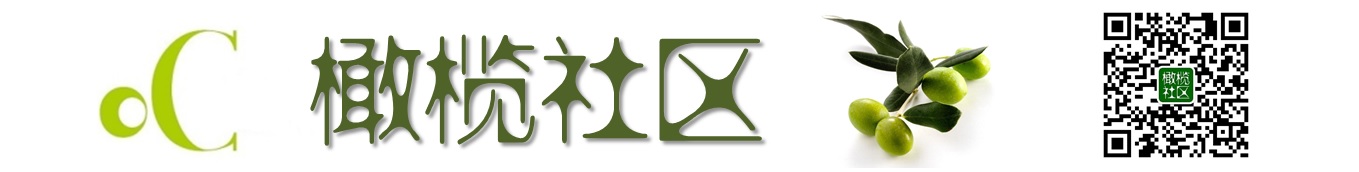臨風
 魯益師( C.S.Lewis )已逝50年,其影響力和作品暢銷度歷久不衰。這與有心人士整理、出版他遺作有關(註1)。“渴慕神”福音機構的約翰.派博牧師(John Stephen Pipe,編註)說,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兩人之一,就是魯益師。2013年“渴慕神”年會的主題,即紀念魯益師(註2)。
魯益師( C.S.Lewis )已逝50年,其影響力和作品暢銷度歷久不衰。這與有心人士整理、出版他遺作有關(註1)。“渴慕神”福音機構的約翰.派博牧師(John Stephen Pipe,編註)說,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兩人之一,就是魯益師。2013年“渴慕神”年會的主題,即紀念魯益師(註2)。
淋漓盡致
魯益師在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從事教學工作29年。1942年,牛津成立了“蘇格拉底學社”。魯益師一直任學社的主席,直到1954年離開牛津,轉往劍橋大學任教。
魯益師是公認的熱愛真理。“蘇格拉底學社”在他的帶領下,成為探討、辯論基督教信仰的一流論壇,是當時牛津最受歡迎的社團。這亦讓我們窺見,魯益師與各種思潮對話的能耐和胸襟。
魯益師護教的風格與路線,與傳統方式不同,他更接近阿奎納、奧古斯丁和伊索。有趣的是,雖然福音界受他的影響至鉅,許多尋求真理的人從他的著作裡得到啟發,突破信仰的瓶頸,皈依基督,然而,他的神學思想與福音界並不十分契合。例如,他對“聖經權威性”的解讀,對“救贖論”的看法,以及對“煉獄”的態度,都與福音派有相當距離。鐘馬田甚至懷疑他不是基督徒(註3)!
魯益師對基督教的貢獻,確實不在神學上,而是在文化對話和護教上。華人基督徒可能都讀過魯益師說理式的《返璞歸真》和他寓言式的《納尼亞傳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體出於同一位作家,令人納悶;而這正是魯益師特殊之處。
巴刻出身牛津,早就知悉魯益師是牛津最有口才的教師。他稱一生受到魯益師的影響極大。1998年,巴刻寫的紀念魯益師百年誕辰的長文中,提到自《返璞歸真》和《地獄來鴻》所受的啟發(註3)。
巴刻特別提到,1945年他在牛津剛信主的時候,讀到魯益師在1933年寫的《朝聖者的退後》(仿《天路歷程》),讓他對西方智識界有了清楚的瞭解。他對這本書愛不釋手,屢屢重讀。
《朝聖者的退後》是1931年底魯益師信主後寫的第一本書,副題是:“對基督教、理性和浪漫主義一個寓言式的辯護”。在第三版的序言裡,魯益師說:“所有精彩的寓言,目的都不是隱藏,而是顯露真理(真實),藉著幻想把內在的世界具體化地表現出來。”從這第一本書,我們就可以看見他後來的寫作方向。
直到今天,他的護教作品還是被福音界視為典範,是競相模仿的對象。例如,紐約救贖主教會凱勒牧師,和英國賴特牧師(N.T. Wright)的護教著作,就是受到他的影響(註4)。然而,這些都遠不如魯益師的來得生動、活潑和通俗。更沒有人能夠像魯益師一樣,把寓言故事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充分傳達了基督教的信息,被孩子與成年人共同喜愛。
年代勢利眼
面對英國神學家的批評,魯益師有一次解釋:“……要麼是高度情緒化的奮興式信仰,要麼就是精英文化中神職人員艱深的論述。這些表達方式,與一般人脫節。我所做的工作就是‘翻譯’,把基督教的教義用一般人所能瞭解的語言表達出來。”(註5)
所謂“一般人”,就是那些受到現代思潮影響的人。現代人總認為:凡是“舊的”,就是過時的。凡是“新的”,不論是新科技,或新想法,都是好的。對這種“年代勢利眼”(chronological snobbery),魯益師深不以為然,認為那是智識上的懶惰(這也是現今流行文化的問題)。魯益師質問:流行的商品在貨架上能擺多久?真正可貴的,是含金量(不變的價值)!
魯益師早期學習上喜歡走捷徑、追潮流,幸得好友歐文.巴菲爾特(Owen Barfield)勸告:不要被“年代勢利眼”蒙蔽。他於是終身奉行。這使得他在智識上獨具慧眼,並用通俗的方式,把這種智慧表達了出來(註6)。
除此無它
派博使用“浪漫”來描述魯益師感性的一面(註2)。他的意思是,魯益師一生都在追求“喜悅”(Joy),這渴求在魯益師的生命中從未間斷。
“喜悅”不同於“快樂”,也不同於“愉快”。偶爾,大自然的壯麗,或是偉大的文學篇章,會觸動人的內心深層,讓人好像能夠觸摸到 “喜悅”,但“喜悅”最終是這個世界無法滿足的、人生更深層的渴求。魯益師說,這渴求非常強烈,勝過其它所有的“飽足”,甚至會帶來痛苦;不過,渴求中也有愉悅。魯益師認為,人類這種渴求指向上帝,指向永生。
研究魯益師的專家,艾倫.雅各布斯(Alan Jacobs)說:“在魯益師一生中,沒有什麼比這種經驗更靠近他心靈的中心了。”另外一位專家克萊德.基爾比(Clyde Kilby)說:“這個主題貫穿他所有著作之中。” 魯益師自己也說:“在某種意義上,我人生的中心故事除此無它。” (註7)
魯益師認為,任何人如果對內在的需求敏銳,也會有同樣的渴求。這個渴求,或許與他對“童話故事”(或稱“神話故事”)的興趣有著密切關係,因為這些故事幫助人的想像力超越現實世界。
經過長期的探索,魯益師於1929年復活節,在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的辦公室裡,由無神論轉變為有神論者——“痛改前非,承認上帝是上帝。我跪下,我禱告。那晚,我很可能是全英國最喪氣,也最不情願,但卻回頭了的浪子。”
有天晚上,他邀請牛津大學教授托爾金(Tolkien)、雨果.戴森(Hugo Dyson)吃晚飯(這兩位都是基督徒)。飯後,他們繼續交談。托爾金到凌晨3點,終於告辭了。魯益師與戴森,又談了一個小時。
在寫給摯友阿瑟.格里夫斯(Arthur Greeves)的信上,魯益師說,這次長談的主要內容是“神話”(myth)。他們在場的幾個人,對各國神話都有很深的造詣。只是,魯益師不能接受耶穌替人“贖罪”的觀念——一個無辜的人,替有罪的人贖罪?這太不公平了。不過,在談話後兩個禮拜,魯益師終於想通了(註6)。
還記得《納尼亞傳奇》嗎?埃德蒙背叛,結果被女巫抓住了。為了拯救埃德蒙,阿斯蘭代替(贖罪)埃德蒙被女巫殺死。正當蘇珊和露西萬分悲痛的時刻,轟然一聲,石桌裂成了兩半。
“這是什麼意思?”蘇珊問道:“難道這又是魔法嗎?”
孩子們聽到背後有個聲音說:“是的,這又是魔法!”竟然是阿斯蘭復活了!
阿斯蘭解釋,在納尼亞形成之前有個魔法——如果有無辜者為了拯救叛徒而被殺害,那麼石桌就會開裂,死亡就會收回它的力量。後來的女巫並不知道。
可是,這個魔法是怎麼產生的?如何運作?故事裡沒有交代。因為“解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阿斯蘭的犧牲,是那些被解救出來的人有了新生,是公義戰勝了邪惡。
在信上,魯益師說:“基督的故事就是一個真神話……這個神話是真實的故事,真正發生過。請記住,這是上帝的神話。其他民族的神話,都是人間的神話……基督教就是上帝藉著‘真實的事件’,把祂自己表露出來。”
魯益師接納了托爾金對神話的觀念。神話不等同“科幻小說”,神話中隱含真理。藉著神話所表達的真理,更為有效。基督教“神話”的中心,就是:耶穌基督的真實故事。
魯益師進一步說:比起故事本身,那些從“真實的神話”所歸納出來的“教條”,是次等的真理。上帝已經用最確切的方式——實際事件,表達出真理。“教條”不過是將其“翻譯”成我們可以把握的“觀念和想法”罷了。
換句話說,魯益師認為,用“神話”方式描述實際歷史事件,就如道成肉身、釘十字架、復活等等,遠比那些“觀念和想法”(教條)更真實、更重要(註6)。這種對“真實的神話”的重視,是魯益師護教的重心。這或許就是他並不重視神學派別的原因。
理性與真理
派博牧師用“理性主義者”,描述魯益師理性訴求的一面(註2)。他並不是說,魯益師“理性至上”,而是魯益師熱衷於用說理的方式來討論信仰,而非權威性的宣告。魯益師認為,理性、邏輯和道德觀都是普世的,是我們用來瞭解上帝所創造的世界的基礎。
然而,魯益師又認為,能思考的頭腦,並非真理最終的詮釋者。理性背後一定有個更完美、更超越的智慧,有個更偉大的奧秘。他說:如果“心思”僅僅依靠“大腦”,“大腦”又僅僅依靠“生物化學”,最後,一切只能歸諸於一組原子毫無意義的流動。頭腦所能想像出來的東西就毫無意義,比不上吹過樹林的微風(註8),因為人本身 “被拆除”了!
理性不能解釋人生的意義,不能指導生存的目的。因此,魯益師向讀者挑明:我們憑理性在現世找不到最終的意義。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可能指向著一個完美的未來。既然現實中的一切,都不能從自己具有意義,那麼,意義一定藏在它處——極可能指向上帝。人如果離開了上帝,就會完全失落。
他的一句名言,非常傳神地表達了這個意思:“我相信基督教,就如我相信太陽升起。並非因為我看見了太陽,而是藉著陽光,我看見了其它一切。”(註8)
在一篇討論基督教與文化的文章裡,他說:“拯救一個靈魂,比出版或是保護世界上所有的史詩和悲劇更為重要。”並且,“生命真正的目的在於榮耀上帝,而榮耀上帝唯一的途徑是拯救人的靈魂”(註2)。我們就此可以看出,魯益師的心放在哪裡。
結語
魯益師在他的作品裡,把為真理辯論的藝術發揮到了極致。他的感性和理性,飛躍的想像力與嚴密的邏輯,這兩個相反的領域,是如此完美地融合,就如左腦和右腦的整合,成為一個平衡的人。
魯益師在《返璞歸真》的序言裡表明,他一生辛苦耕耘的目的,就是為基督教辯護、解釋(翻譯),以幫助那些沒有信仰的“鄰居”。因為他看到,現代文化鼓勵人停止思考,鼓勵人浮誇、追求新穎,排斥一切舊有的價值和知識。他希望引導這個世界張開眼睛,看到真正的美、真正的善。
魯益師的傳記作者喬治.瑟爾(George Sayer)提到,他的女兒讀完《納尼亞傳奇》以後,放聲大哭,說:“我不想繼續活在這個世界。我希望與阿斯蘭一同活在納尼亞。”
我有同樣的讀後感。我嚮往耶穌基督同在的世界。魯益師的筆,讓我感受到一個更可親近的上帝,一個更值得追求的彼岸。這是我在其它地方未曾感受到的。就如瑟爾安慰女兒的話:“親愛的,有一天你將會與阿斯蘭同住。”這不也是我心裡最深的盼望嗎?
註:
1. 主要有Walter Hooper,Clyde Kilby。特別推薦Alan Jacobs, The Narnian,和 Jack, A Life of C.S. Lewis。不推薦A. N. Wilson帶有偏見的C.S. Lewis: A Biography。
2. 參派博兩篇演講:a) “Lessons from an Inconsolable Soul: Learning from the Mind and Heart of C.S. Lewis,” Desiring God Conference for Pastors, 2010. b) “C.S. Lewis, Romantic Rationalist: How His Path to Christ Shaped His Life and Ministry,” Desiring God 2013 National Conference.
3. J.I. Packer, “Still Surprised by Lewis,” Christianity Today, 1998-9-7.
在2013年發表的一篇訪談中,巴刻認為自己不是(系統)神學家,而是“解惑者”(catechist)。這或許是他能夠欣賞魯益師的原因之一。
4. 參凱勒,《我為什麼相信》;賴特,《純.基督教》。
5. 魯益師回應自由派神學家Norman Pittenger 1958年的批評: “Rejoinder to Dr. Pittenger,” in God in the Dock, pp. 181, 183。派博在演講中引用。
6. Alan Jacobs, The Narnian(San Francisco: Harper, 2005).
7. C.S. Lewis, Surprised by Joy(Harcourt, 1955).
8. C.S. Lewis, “Is Theology Poetry?”Essay Collection and Other Short Pieces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0).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