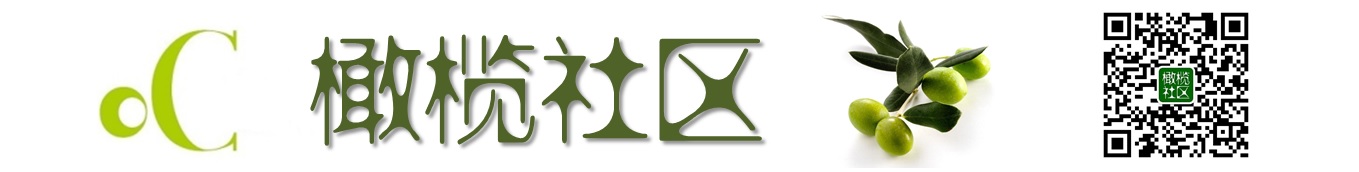本文原刊於《舉目》54期
謝文郁
 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興奮,令人目眩。中國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這樣的口號深入人心。從此,中國這塊土地上,瀰漫著“人定勝天”的精神和勇氣。
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興奮,令人目眩。中國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這樣的口號深入人心。從此,中國這塊土地上,瀰漫著“人定勝天”的精神和勇氣。
在理論上,這股精神和勇氣在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了立足點。在實踐上,“大躍進運動”(1958-60年)把這股精神和勇氣傳染給每一位中國人。於是,中國人開始生活在一個完完全全的人文主義氛圍中﹗!
對於當時的中國基督徒來說,這是一種信心挑戰。許多基督徒不知不覺也受了影響了,或離開了教會,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傳教士們的憂心成了現實。早在20年代中期,隨著非基運動的廣泛展開,傳教士愈來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情結,感受到這一情結對基督福音的嚴重阻攔,他們猶如面對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牆,而無能為力。於是,他們呼籲跨宗派的聯合禱告,求神親自拆毀這堵牆。
然而,歷史發展似乎和所期望的發展背道而馳 。他們問,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西化運動,是高舉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義運動。這場西化運動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歷史舞台的前台,並在新中國主導了中國文化的話語權。──上帝在聽我們的禱告嗎?還是說,我們的禱告出了問題?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後,中國教會出現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分化。按照中國的法律,“家庭教會”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會”無法公開聚會,其活動能力和範圍 都大大收縮。他們無法在公開場合,向中國人展現神的榮耀。然而,他們秘密聚會,認為自己是神所揀選的“小群”,心甘情願為神受苦。
“三自教會”則因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開活動。雖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小,但是,三自教會仍然在社會的視野中。三自教會中的許多人相信,他們還在為神做見證,他們參與三自運動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對於新政府來說,基督教教會並不是一股強大力量。在通過三自運動解決了基督教問題之後,他們幾乎不把基督教當回事。此刻還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經濟和 軍事上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儘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極端的人文主義情結中,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進一步深化 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趕超世界發達國家,成了中國社會的前進動力。受政府宣傳的影響,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眼中,基督徒屬於落後、跟不上形勢之人。基督教是一種迷信,必將被歷史拋棄。
在這種形勢下,在公開場合宣傳基督教,等於把自己公開當作笑柄。迫於政治壓力,不但年輕人,即使那些屬靈前輩,也無法在公開場合宣告福音。王國顯弟兄在回憶 錄《行過了死蔭的幽谷》一書中提到, 1957年他從牢裡釋放出來,回到廣州大馬站福音會堂(1950,林獻羔創立):“那時教會傳出的訊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帶領神的兒女繼續要活在神的臉 光中。我們更孤單了,但是卻激勵了許多在各地的神的兒女。他們知道我們仍舊孤軍作戰,他們寫信來與我們表同情,我們也因此得安慰。”(頁150)不久,王 國顯就向政府申請出國。
那時中國的基督徒(不管是屬於家庭教會,還是三自教會),能夠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為神做見證了。能為基督的名吶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滅”
進入60年代,經歷了 “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之後,新政府覺得已經比較穩固地控制了社會,在政治上略微放鬆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在大躍進運動中的激進、冒進,中國 經濟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害。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中國政治發生了重要變化: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管政局。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府為了經濟的發展,允許農村地區有較大的自主性。於是,在60年代的頭幾年裡,有些農村出現了遊行傳道人。這些遊行傳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們的活動亦十分有限──當時教會的傳道人,或者入獄,或者受到控制,無法出來傳道。
1963年,中國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略略緩過了一口氣。這是一場天災加人禍。如果中國人能夠靜心反省,不難認識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難從中汲取教訓、學會謙卑。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人不具備這種反省能力。
在馬克思主義主導下,人文主義已經在中國膨脹。中國大陸的各種宗教,都順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理說,宗教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然而,1963-1965年 這段時間,中國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紅旗》、《新建設》、上海《文匯報》等)上,刊登了相當激烈的“宗教大辯論”。這場辯論涉及了宗教定義、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問題,可是卻沒有宗教人士的參與,基督徒更是沒有發言權。
在辯論中,就宗教政策問題,形成了兩個派別,即所謂的溫和派與激進派。雙方都堅持唯物史觀的無神論,不過,溫和派(以對藏傳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學家牙含章為代表)認為,從唯物史觀出發,任何宗教都不過是歷史 進程中的一種現象。它的產生有其歷史條件,消亡也有歷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採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讓它自行消亡。
激進派則以遊游驤(馬 克思主義學者,後跟隨趙樸初學佛學;改革開放後進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劉俊望等為代表強調,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必然和當下的馬克思主義勢不兩立。因此,政府必須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和各 種宗教進行鬥爭,儘快消滅宗教現象,確保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
很清楚,無論是哪種立場,其目的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消滅宗教﹗!
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場此辯論中的激進派理論,終於成為政府宗教政策決策的根據。
新中國的第2個10年,其政治趨向是要消滅基督教教會(無論是三自教會,還是家庭教會)。其實,這並非僅僅針對基督教,其他宗教也感受到生存威脅。進一步 說,不僅是宗教,所有不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脅。總之,政府統戰工作的核心,是在全國確立統一的意識形態。至於基督教,最好在中國永遠消 失。
艱難中苦尋出路
上帝為何什麼允許這種事發生?家庭教會的基督徒認為:神把他們分 別為聖,揀選他們為得救的“小群”。他們的秘密聚會一直沒有從未停止。許多老傳道人回憶,為了不讓人發現,他們在午夜或凌晨進行聚會。他們堅信,這個世界 遲早都要廢去,但是神的話語永存。只要堅持聚會,他們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
他們的活動是秘密的,且在小範圍內,政府似乎沒有專門關注他們。在公開場合,他們也不再宣稱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在社會視野中,他們消失了。
三自教會在60年代的頭幾年,場面上仍然相當熱鬧。他們可以公開聚會,公開舉行一些宗教活動。但是,這些活動,都必須配合政府的政治意圖,和官方意識形態保持一致──官方意識形態的主要特徵,是與基督信仰格格不入的無神論。
對於許多三自教會領袖來說,他們加入三自教會的目的,一是為了自己的生存,二是為了教會能夠公開聚會、為神做見證。現在,他們必須配合政府消滅基督教的總方針,這樣下去,他們如何能夠為神作見證?於是,許多加入三自教會的基督徒開始反思。然而,他們找不到出路。
當時中國基督教界的神學泰斗賈玉銘,為了維持他所創辦的上海靈修院,參加了三自教會。結果是,靈修院中的優秀神學人才,或被迫離開,或鋃鐺入獄。最終,賈玉銘非但沒有保住上海靈修院,反而使自己走上一條不歸之路,連禱告都感覺不到力量。正符合了當時政府宗教政策之目的。
這便是三自教會的困境。我們可以從一些縣志或市志中讀到相關的記載。根據《廈門市志》:“1956年12月17日,召開廈門市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第二屆代表會 議。正式代表173人,特邀代表23人。代表中有4個教派和23個基督教單位。1957年後,基督教界受到各種政治運動的衝擊,活動漸不正常。1966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教堂被‘砸’、被抄,教牧人員和教徒被‘批鬥’,宗教活動基本停止。”
不同地區的縣志和市志,在涉及基督教這段歷史時,幾乎用了相同的語言。從1954年到1966年,三自教會還沒有來得及形成自己的性格,就在新中國的政治漩渦中淹沒了。
家庭教會的秘密聚會,無法為神公開做見證;三自教會的公開聚會,也未能維持長久。中國教會在死蔭幽谷中行走。三自運動催生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兩種存在形式,但是,時代的急劇變化沒有給他們深思熟慮的機會,也沒有給他們從容回應的餘地。
很快,中國就進入一場浩劫,基督徒則經歷了更嚴酷的政治生活。面對這場狂風暴雨,中國基督徒能夠持守自己的基督信仰、走出這死蔭幽谷嗎?神要對中國基督徒說什麼呢?神要對中國人說什麼呢?(未完待續)
作者來自中國,現為北美神學院教授。
圖片來源:http://sc.chinaz.com/tup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