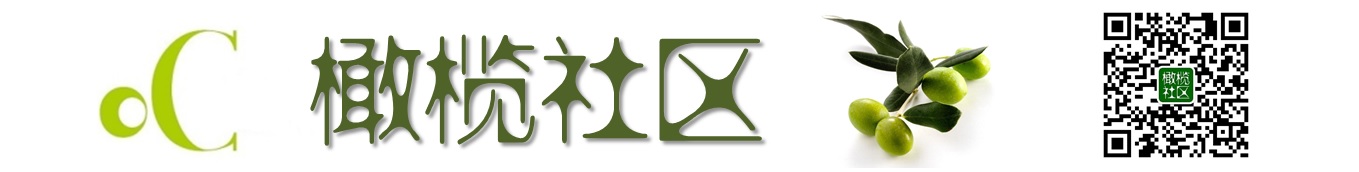雨峰
按照中国大陆惯用的说法,我属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而且,我还是受“党的教育”多年,拥有好几个荣誉头衔,并负有一定职责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朝着既定的方向再走一段路程,我也许会有更高的职位。
从世俗的观念讲,事业、地位、声望和某种权力,似乎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物质利益也必然会不断增加。作为一个生在穷山沟,长在“黑五类”家庭,历尽困苦艰辛、颠沛坎坷的人,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应该知足了。
然而,我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一切,甘愿从零开始,再一次经历严峻的试炼,走一条险象环生的崎岖小路,去叩那个为世人视为畏途的“窄门”。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不满意我在中国大陆所能享有的物质条件,也不是因为不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恰恰相反,我对物质生活并无更高的奢求,想到百分之80以上的同胞还处在相当穷困的状况之下(与当今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想到我自己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所经历过的极度贫困,我始终认为自己眼下的生活已经相当优裕了。在事业方面,我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最符合我心愿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十几年来,我也算取得了一些成绩,赢得了学术界认可。
我的母亲是一位极为虔诚、热心的基督徒。小的时候常听她祷告,读《圣经》,唱赞美诗,作见证和解说《圣经》中的故事。母亲的教导在我心中埋下了追求真理的种籽,并成为我多年以后属灵生命得以复活的契机。
母亲去世后,她播在我心中的种籽也处在压抑之下,未能及时发芽,成长。
但是它自始自终,一直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田里,等待有一天遇到丰足的甘霖,得着和熙的春风,迎来适宜的气候,便要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然而,我在学校里所接受的教育,却迫使我远离母亲的信仰。每一篇课文,每一堂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反复复灌输给我们的信念是,天地之间没有比“共产党”、“毛主席”更伟大的了。只要信靠这两尊“大神”,中国人民总有一天要建成“地上的天堂”—共产主义社会,而宗教信仰只是“封建迷信”、“精神鸦片”,应该像垃圾一样把它清除掉。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给许多人带来太多不幸,给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破坏;我自己,我的两个姐姐和许多人一样,甚至失去了继续上学读书的机会,不得不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我也曾对共产主义产生过怀疑。但是,因为再没有人为我讲解《圣经》的真理,除了共产主义的理念之外别无选择。
“文革”结束后,我才得到了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机会。在大学读书时,我再次接受系统的意识形态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思考之后,还是被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性所折服,重新确立了对马克斯主义的信仰。
我当时简单地认为,过去所发生的种种灾难,都是毛主席个人的错误和“四人帮”的阴谋所造成的“失误”。共产党是好的,马列主义是正确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唯一希望。这当然是一种很方便的结论,以便使自己得到某种内心的平静。
无论如何,这种看法使我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能够一心一意地读书,以补回过去在求知方面所受的亏空。从1978年春到1988年秋,我连续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学位,并开始写一部颇有雄心的学术著作。
正当我的书写到一半时,1989年的事件发生了,维持了十年的心里平衡被彻底打乱了。严酷的事实,再一次把我和许多同代人推入了失望的深渊,这次的失望比“文革”中那次更深刻,更难以修复,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哲学和伦理的根基上产生了动摇。
我的痛苦竟如此沉重,甚至使我无心从事学术研究。已经写成一半的书稿也搁置起来,再也继续不下去了。因为,假如自己所预定的哲学前提不复存在,整个立论不就成了建在流沙上的宫殿了吗?哀莫大于心死。我不但失去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也失去了对教学的热情。
假如我认真教导的学生有朝一日也和我今天一样陷入精神困境,那又由谁来担当其罪呢?更何况自己又何以立教,何以为信呢?古人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道”已经垮下来了,我这个“师”也就无法再做下去了。
正在这个困惑彷徨的关头,我得到了一个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当飞机会升至万米高空的时候,从窗口向下俯视,便看到无边无际的灰色—冬天的田野;绵延起伏,因缺少植物而裸露着躯体的山嶙;那泛着灰黄色的神州第二大河;还有黄土山头后面那更加广阔的沙漠和戈壁滩。
这景象给我的视觉以巨大的刺激和震撼,那种强烈的感觉一直贯穿到我的五脏六腑和我全身的神经系统,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可言状的沉痛和绝望。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二千多年前,那位高吟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踏上“诛暴秦”的征程,决心与秦始皇同归于尽的荆轲。
真奇怪,我并不是要去刺杀什么暴君,也不是要“一去不还”,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热爱这片贫瘠的土地,我热爱这里的云云众生,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学生,我的同事和亲友,更何况还有我的家,我的妻子和女儿,我怎么能够抛下这一切,而“一去不还”呢?然而,那种沉重的,几乎有点悲壮的情绪却一直伴随着我,令人无法排解。也许在离别亲人,远渡重洋,即将投入异国他乡那完全陌生的环境时,心情难免沉重一点吧?
也许我的心灵深处已经预感到了将要发生什么突变吧?不过,有一点感受是极清晰,极真切的,那就是我当时的精神状况和飞机下方那片灰色的,了无生机的戈壁滩相映成趣,形成了一幅完整统一,难割难分的立体画面。
我于1990年秋天,到了康州州立中央大学。在那里认识的一位台湾学生,介绍我参加查经聚会,并坚持不懈地每个主日都开车接送我。聚会由一位几年前移居美国的中国工程师和先生主持,虽然我参加了每个主日的聚会,却对《圣经》没有任何感悟。
当时,我真是心里刚硬,顽劣无比,觉得这种聚会简直就和“政治学习”一模一样。真正使我感动的是那些基督徒对人的真诚、热情和友爱。
外表上看,他们是同样的中国人,而内心却完全不同。经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强迫参加的“学习会”,大多数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中国人,学会了怀疑一切人,包括自己的朋友以至亲人,他们一个个几乎变成了罗马神话中的“双面亚努斯”(Janus),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二重人格”(dual personality)。
一张虚假的脸,用于在公共场合表明自己“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而另一张真实的脸,则隐藏在私人生活的阴影之中,用堂而皇之的政治口号来掩盖充满
私欲的心灵。可是,那些信仰基督的中国人,互相之间却有着完全的信任,对人能坦诚相待,关怀至微。
一年后回国时,我仍然未能皈依基督。但是,我的心境和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回国后,精神上的苦闷并未消失,不过,和过去不同的是,我可以常常翻阅《圣经》,试图从中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在美国参加查经聚会时听到的许多见证,也不断引导着我的思绪,有时候,我彷佛看到了一线光明,但更多的时候却被无穷无尽的疑问所困扰,使我内心更加难以安宁。
在这段时间里,我想得最多的是母亲活着时的情景,母亲对信仰的坚定和热忱,对于传福音的强烈使命感,对子女的谆谆教导,在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和逼迫试炼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和巨大勇气,对亲朋邻舍所具有的真诚关怀,对伤害她、污辱她、迫害她、折磨她的人所具有的无限宽容等等。
小的时候生活在母爱的荫庇之下,并不感到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冷漠、严酷和虚假。而今,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坎坷之后,更体会到母亲的爱深沉如大海。然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母亲从哪里获得那么大的精神力量,以至于在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依然能够以无穷的爱心面对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结论几乎是无可回避的。
很明显,信仰是我母亲生活的核心,也是她力量的源泉,信仰给了她巨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够使她渡过难以描述的艰辛、屈辱、困乏和病痛,在担负着抚养二子三女的重担之外,还尽力帮助别人,不失时机的传扬福音,争得更多的人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也许是由于对母亲的回忆占据了我太多的心思意念,日有所想,夜有所梦的缘故,或者是主耶稣想借着一个梦向我传达某种信息。无论是何种原因都不要紧,这里我要说的是,我做的一个梦在我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可算是一个里程碑。如果说在那以前,我还只是个三心二意的慕道者的话,而在那以后,我才开始认真地探究《圣经》的真理,力图为我头脑中出现的各种疑问寻找答案。在那以前,我还只是一个丧失了信念的唯物主义者;而在那以后,我已经成了一个专心一意走上“天路历程”的朝圣者。
我所做的那个梦,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大概是1992年春天的某一天,我睡得很晚,早上醒得却很早,我心想,还应该再睡一会儿,这一睡,就进入了一个美妙无比的梦。在梦中,我清晰无误地见到了去世已有二十余年的母亲,她似乎比生时更年轻,更美丽,一如既往地豁达、欢欣、自信、刚强。她就像对孩提时代的我一样,用我的乳名呼唤我说:“孩子啊,你不可以脏成这个样子。来,跟我来,让我为你洗一洗。”我也彷佛回到了幼年时代,欣喜地跟母亲来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边,母亲命我走进溪水之中,便开始为我洗浴。
这一觉醒来,我感到了无比的幸福,真有一种返老还童的心情。我立刻想到一个英文单词—baptism(受浸),我当时认定,母亲要我受浸,以便除去我浑身的污秽,她一定是受命而来,向我传达无上的旨意。看看自己,真是污秽无比。自从母亲去世后,我被训练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战士”,成了向圣洁的,至善至美的上帝挑战的狂妄之徒。“人定胜天”、“我们能在地上建立天国”,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战斗口号。我不再敬畏至高无上的耶和华上帝,而只服从地上的权威。我越来越深地陷入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越来越把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争取更多名利、地位、头衔和特权,当成人生的最高目的。回头一看,我已经与纯洁善良的童年判若两人,浑身上下沾满了俗世间的各种秽物,散发着逼人的臭气,难怪母亲要为我洗浴,要除去我一身的污秽。
我不懂得作梦的神学意义,我只是从直觉上接受了这个梦带给我的启示。她在我属灵生活的道路上确实引发了奇妙的转变。
三年后,我再次来到北美。到加拿大温哥华后不久,偶然间找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国语团契。每周一次,几位从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同两位美国人在一起,用国语读《圣经》,唱赞美歌,谈论信心上的见证,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牧师和众多弟兄姊妹,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关爱和鼓励。参加维真神学院中国学生学者团契的查经学习和讨论,也帮助我解除了许多思想上的疑问和障碍。主内弟兄姊妹给我的许多书籍和刊物以及我从图书馆借的有关书刊,使我对自己根深蒂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进行了一次清理。最重要的是,我逐步学会了通过默祷求主耶稣带领我走追求真理的道路。终于,我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从内心里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也坚信已被主所接纳,1994年三月27日,我在福源堂听叶医生的证道,当她说,“如果你愿意现在就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请举起你的手”时,我感到再也不能抗拒我心灵的召唤。于是,我在上帝的荣耀中,在主耶稣的大爱中,坚决地举起了右手。
感谢主,祂在暗中牵着我的手,让我经历了诸般的诱惑和试炼,把我一步一步地带离了罪的深渊,最后归向了祂。1989年初夏,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把我从迷梦中惊醒,使我突然间发现了人生的空虚、荒谬、丑恶和残酷无情。原有的信仰土崩瓦解之后,追求新的信仰便成了当务之急,我涉猎过西方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科学主义;东方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说和伊斯兰教。虽然,我也从中得到了不少知识,却没有一样能够满足我心灵的饥渴,只有在主耶稣的永恒生命里面,我的心灵才得到了完全的平安。
也感谢主赐给我一位热爱主的母亲,她没有给我留下田产家业,也没有送过我贵重的礼物,但她却为我留下了最丰富的遗产—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颗追求真理的种籽,一颗虽然遭到长期压抑,但一遇到适宜的温度、湿度便会勃发生机,茁壮成长的灵命的种籽。作为父母,这实在是能够留给子女的最宝贵的遗产了,因为它永不朽坏,永不失色。
迈出了第二步
受洗归主,有了新的生命,这是我属灵生活的起步。接着,我还迈出了第二步,就是摆上自己,为主所用。
我自己的愿望是做文字布道的工作。我能迈出这一步,也经过了十分艰难的属灵挣扎。我永远不会忘记1994年八月30日我在多伦多一个公园里所作的祷告,当时,我正在那里访学。在那时,我虽然已经收到了两所神学院的录取通知,也收到了美国一家基金会提供资助的承诺,但是我自己却信心不足,成天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要跟随主耶稣,就要像祂的门徒彼得和约翰那样,毫不犹豫地抛下渔船和鱼网,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已经握了十几年的教鞭。一想到那些熟悉的亲朋好友,同事和同学,特别是想到自己对那些学生所承担的责任,我的心就感到非常沉重。
那天我半夜三点醒来,再也无法入睡,一早去图书馆,也不能静下心来读书。于是,我干脆放下书本,信步走进一处公园,坐在一棵状如华盖的大树底下,闭目祷告。在那次祷告中,我得到了两条信息:第一条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路加20:25)。我已经为该撒(国家)尽了15年的义务,我的后半生应该为主耶稣尽点绵薄之力了。第二条信息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6:34)。这两条信息使我心中阴霾尽除,我不再为已失去或将要失去的俗世的东西而惋惜,也不再为明天的艰辛和坎坷而忧虑,我决心把自己和全家人的未来,完完全全地交托在上帝全能的手中,坚信凡祂所应许的,祂必成就
本文选自《海外校园》第12期。作者来自甘肃省,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