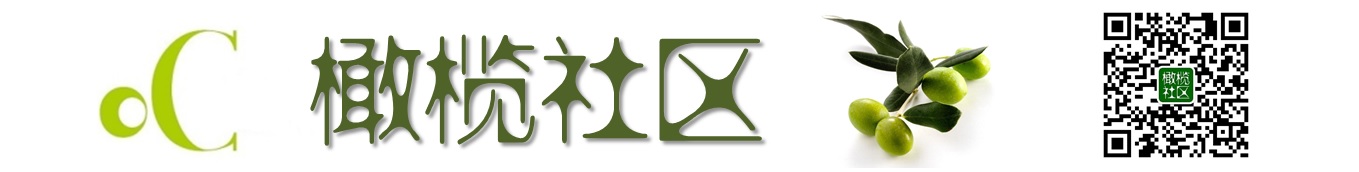星語星願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享有“雨巷詩人”美譽的戴望舒,在上世紀假《樂園鳥》詩句噴薄情懷:“華羽的樂園鳥,自從亞當、夏娃被逐後,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
(一)
“瘋子領瞎子走路,本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病態。一個人即使沒有眼睛,也可以看見這個世界的罪惡。”(《李爾王》第4幕)“時代的靈魂”莎士比亞,遠在16世紀,便一針見血地剖白了這個癲狂世界。
入職未深,我便如處於一個喧囂吵嚷、互奉杯酒的“年會”,似乎所有人的目標都是:酩酊而歸。一張以各種“潛規則”織就的巨網,將求生計之人困囿其中,成就外表光鮮,實則醉酒糜爛的人生。
這確是荒野,一無所剩,遍野哀鴻。浮沉其間,我忽而想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韋爾霍文斯基的話,“然而現在卻必須有一代或兩代腐化墮落的人;需要那種 駭人聽聞、卑鄙齷齪的腐化墮落,把人變成可惡的、膽怯的、殘忍的、自私的敗類──這就是現在所需要的。此外還需要一點‘鮮血’,以便使我們漸漸習慣。”
思維被拉伸到此,不由想起宮崎峻的《千與千尋》中鬼魔扶搖的場景,慾望的毒瘤隱蔽在靜謐的街頭、豐盛的暗處;黑暗上籠,媚燈搖曳,各種樣態的怪物粉墨登場,逢迎阿諛,貪婪嗜血在肆無忌憚地鋪陳開來……
令人咂舌的是,現實世界將影片的場景盡數重現:我們見著人類品格整體的缺乏及至赤貧,人類內心整體的無助及至絕望,人類尊貴身分被拉扯,於是人類墮落,再墮落。
我仰天號啕控訴:上帝,你為何使我跌撞於罪孽,壓傷我的心呢?
先知以西結催淚若雨的話,亦在心間蕩浮:“……他們吃飯必憂慮,喝水必驚惶。因其中居住的眾人所行強暴的事,這地必然荒廢,一無所存……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結》12:19-20)
(二)
諾貝爾得主、詩人黑塞,面向一貧若洗的世界,便將生活哲學訴諸《荒原狼》,“回頭根本沒有路,既回不到狼那裡,也回不到孩童時代。”
當那個來自蘇北的車間阿姨,操著並不熟稔的普通話,滿了擔心和掛念地向我絮叨她留守在家的兩個孩子;當那位雙手皺裂的叔叔,神情憂悒地回答我:“春節不回家了,可以省一些路費”,我有種胸口被堵塞的感受。
當那幾個稚氣未脫的孩子,在近夜時分來工廠求職,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未諳世事的他們,已開始用雙肩擔負生計;當我義憤填膺地因工資拖欠問題,翻找《勞動法》條款,以期捍衛權利的時候,他們也只是在冬日密陽下,再一次地眯起眼睛,陷於沉默,後又無奈地追鬧成一團……
盧梭說:每個人在一出生時,口裡都含有一枚金幣,一面是自由,一面是平等。然而舉目,滿了眼的卻是戴著鋃鐺鐐銬、左顧右盼的人,站於枯草污臭之地,夜以繼日地重覆著無助和迷茫,或許尋找著出路,或許沒有。
一位姐妹發文,說起她對街頭行乞者的關注。她對於“社會邊緣人”有特別的感動,因為“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林前》1:28-31)
我不由產生一種愧疚之感──當我身處各種石化粉塵彌散的生產車間,與四面八方而來的農民工一起,塑化、美飾產品的時候,我內心洶湧的只是個人逃離的衝動。我自認我所闖入的或許是一場錯誤,這裡是我無力承負的罪孽之穴,也是無法回應我個人期待之境。
當大學室友、兒時同窗、主內弟兄,依次向我伸出“工作橄欖枝”之時,我似乎積攢了足夠的自我正義說:“我要離開這裡。”可若我一面說“我信”,一面又無視上帝,所能成就的,也只有生命的分裂。
而當我望向上帝,我看見我自己本從“埃及”起行。我看見摩西跟隨那位應許他說“我要帶你去迦南”的上帝,一路曠野,一路風塵,一路歌。我看見那位恩主披著真 理之光,攜孤單、困倦、凌辱、被棄,向著各各他走去。祂雖因鞭傷步履時有蹣跚,卻不躊躇,甘願以捨己之愛拆撤神人之間的隔垣,以換取罪惡權勢之下的靈魂。 祂向愚昧無知的罪人宣告,向麻木無望的世人宣告,亦向跟隨了祂卻依然驚魂不定的門徒宣告:看哪,我要將一切都更新了!(參《啟》21:5)
(三)
我要傳揚,要竭力揚聲!“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路》4:18-19)
覓機重讀《使徒行傳》,俯首於地圖,隨著恩主的門徒,一次接一次地出行。當我留心保羅的3次旅程,再次瞠目於他因福音被毆打、斬首……我為之扼腕之餘,卻發 現他錚錚作答:“我不以性命為念”,“我已將萬事看做糞土,唯以得著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參《徒》20:24,《腓》3:8)。
托爾金寫與摯友:“我們出生在一個黑暗的時代,這並不是我們應該身處的時代。但我們還是有令人感到安慰的事情: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不會明白我們熱愛的東西,至 少不會知道得那麼多。我想只有離水的魚兒才能對水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基督徒是離水的魚,與他們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我們是英國清教徒、異鄉人、被放逐者,但我們很快就會回到家鄉……”我們匍匐於罪惡以及由此生發的苦難之中,然而確有一座天上的城,供我們期盼和渴想。
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如此評述杜氏《白痴》裡的梅思金公爵,“他執意要進入惡的世界,愛與惡的爭鬥將是一無所得的犧牲……以深摯的愛償還現世惡中的人遭受的一切。”
有書評說,梅思金公爵是杜氏筆下的、明確的基督大愛的具現。當他出走山林,帶著聖潔靈魂重涉世界之時,“他的一切激動,一切疑惑,一切不安,一下子都平復了,融化成一種高度的寧靜。在這種寧靜裡,充滿明朗、和諧的快樂和希望,充滿理性和真正的原因。”
C.S.魯益士在寫給孩子們的信札裡,透露著他更傾愛《裸顏》的情懷,裡面的賽姬,在獲得上帝垂顧之時,歡愉地說:“我們的心為什麼不雀躍呢?……”
是的,我們的心為什麼不雀躍呢?
作者目前供職於上海一家律師事務所。
圖片來源:http://www.bigfoto.com/